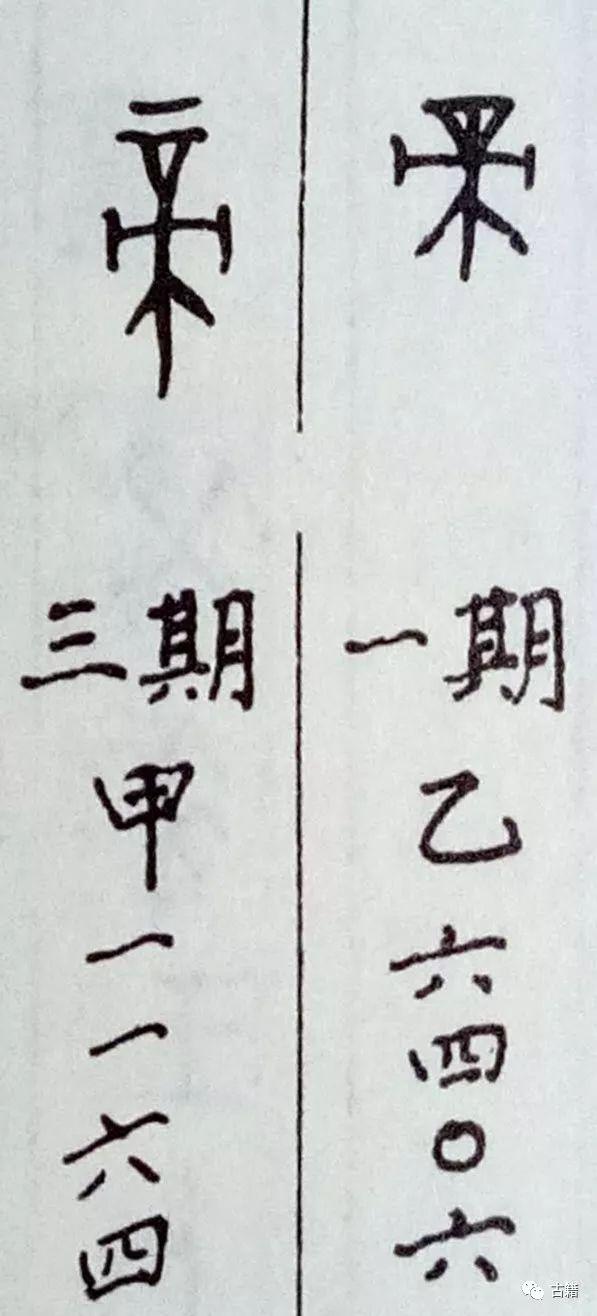
“帝”之崇拜始见于殷墟卜辞,最晚自武丁时已成为传统信仰中至关重要的一节。自近代来,“帝”与祖先神之关系便聚讼纷纭,从傅斯年先生提出“商人的帝即是帝喾,就是商人的高祖”这一说法后,学者的讨论多集中于商、西周时期“帝”与祖先的关系,并多以为“帝”称表示始祖,而后黄帝等称谓则是因其为始祖而加以“帝”称。这一问题经胡厚宣、朱凤瀚、晁福林等先生讨论,一般认为至西周时期,“帝”的形象已较为明确,即“帝”为单独的天神,而非明确的宗族神。在春秋时期,专属于天神上帝的“帝”被用以称呼上古祖先、英雄,这一现象虽被关注,但如顾颉刚、徐旭生等先生仅论其作为尊号比拟于天神上帝,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赋予神圣化的色彩,并未能深入论述其原因及意义①。近年晁福林先生论及此问题则云:“古史的传说时代(亦即五帝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去世后成为天神,被尊为‘帝’。”[1]李明阳先生则从殷周信仰比较的角度专论春秋时“帝”的职能演变与人神关系的转型,提出帝的形象鲜活的同时,神权却趋于衰落,并不再为史官所垄断,成为君子群体构建自身话语权力的背景。其论聚焦于春秋时期的“帝”这一过去未及申论的问题,对其权责形象变化都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以为“周代继承帝的王业,观念上也信奉上帝和尊敬殷先王。春秋时期基于当时的神话传说和现实需耍,建构‘五帝’信仰”[2]。对其中变化原因亦未加申论。然而“祖先”如何与“天帝”发生联系这一问题,对于先秦阶段神灵信仰、人神关系的构建仍有重要价值,春秋时期恰为其关键阶段,故笔者拟就此略陈己见。
一、“人帝”之称开始出现
考察此阶段“帝”身份之变化,可以结合此时帝与其他神灵的关系进行考虑。仔细梳理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则可以看出先人被称为“帝”的情况在春秋时已经出现,且其在叙事中代表的形象仍然是人祖,而非天神。
文献中作为人祖的“帝”被反复称引的非“黄帝”莫属,赤帝或炎帝之称则远逊于他,而且提及炎帝之内容往往与黄帝密切相关,故而将此两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这两种称谓始见于《逸周书·尝麦》:
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②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常③,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此篇记述了王关于修改刑书的文诰,在诰命中追述了两件与制刑有关的故事,第一件即是黄帝伐蚩尤,另一件则是启子五观之乱。两件事情均以平定叛乱为主题,这是由于上古兵刑不分,征讨叛乱即是刑律的一部分。如《汉书·刑法志》谓:“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3]1079意思便是礼体现天所制定之秩序,刑体现的则是天对有罪的征讨。因此在诰命开篇援引这两则征伐叛乱的故事以为下面的宣告刑书等内容张本。
这段话难以确解,其中赤帝应是“以火纪”的炎帝,“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丁宗洛据《蔡仲郎集·胡黄二公赞》“诞育二后”补“诞”字,并谓二后即是下文之赤帝、黄帝[4]731。“诞”见于《诗经·大雅·生民》“诞弥厥月”,马瑞辰通释谓:“诞为语词,训大亦语词。”[5]875所谓诞作即类似于《孟子》引《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之意,“后”即君长之称。尽管对于赤帝和黄帝的身份注者仍有争议,但各家对这段话大意的理解却颇为趋同:从前在天地初分的时候,上天为民设立了两位君长,即下文所说之赤帝与黄帝,使他们陈立彝伦法度,以此治理天下。天又命赤帝分派二卿治理天下,命令蚩尤辅佐少昊④,天让他们治理四方,完成交给的任务。但是,蚩尤却欲把赤帝逐走,与其在涿鹿之地大战,使得九方之民靡有孑遗。赤帝害怕,请黄帝支援,这才把蚩尤捉住,在冀州之野将他杀掉。从这个传说里可以看到,赤帝与黄帝地位相当,蚩尤也与之相差无几。赤帝的影响似乎还要大些,只是后来被蚩尤打败,势力和影响才稍减。
关于《逸周书·尝麦》篇的制作时代,李学勤先生认为《尝麦》的文字很多地方类似西周较早的金文,篇中引述黄帝、蚩尤以及启之五子等故事,与《吕刑》穆王讲夅尤作乱、苗民弗用灵等相呼应,其时代当相去不远,有可能是穆王初年的作品[6]94。张怀通先生则结合官职名称认为“《尝麦》最初当成于西周早期”,但又指出“《尝麦》经过西周春秋时代的流传,到战国时代基本定型时,其语言文字已经变得较为通俗,并且有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官职羼入其中”[7]。如果单从“刑书”、官职的地位权责看,其内容无疑可以追溯至西周中期,而且其记述诰命流程的部分文字古朴,对于当时场景的描述也与铜器铭文中册命的内容十分相似,其所记录的这次诰命活动应当就是源于当时史官的现场记录。但是,具体至周王所援引的这两则古史故事,由于叙事性较强,文字也比上下的史料记录易懂许多,其中“五帝”等称谓亦不见于西周早中期的文献,则此古史故事应当是经过春秋乃至战国时期的不断修补、引申而成,“黄帝”“赤帝”之称谓的出现也并不会早于西周晚期。
在现今所见的甲骨卜辞及可靠的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献里都见不到“黄帝”之踪影,所以可以推测,“黄帝”“赤帝”等是西周中期追溯古史时才见诸史载。此前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录其相关的故事,但是人物的名称、故事的象征意义等则可能是西周中期称引时根据当时的习惯与需要来确定的。
此时提及之黄帝、赤帝均为人,而非天神之属。天立之为万民之君长,意义即类似于天授命文王,使之治理天下。在这个故事中,二者也并没体现出任何神异的色彩,完全是人君的形象。可以对比的是约与此篇同时的《尚书·吕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与“主名山川”一句含义有关的是《史记·夏本纪》“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8]82。后人多从此解说,以主为神主,则禹为山川之神主。但是对比伯夷、稷的功绩,可以看出此处三人的功绩都是针对民而言,是忧民、救民之功。伯夷制定典常,制刑罚管理人民;稷赐民嘉种,教民勉力农耕,后一句都是对前面行为的补充。而将“主名山川”解释为禹是山川神主,则与论伯夷、稷中后一句皆是讲二人功绩不合。因此“主名山川”并不是“平水土”的结果,而是对平水土的补充。伪孔传释为:“禹治洪水,山川无名者主名之。”戴钧衡亦云:“‘主名山川’者,分疆域,表镇望,《禹贡》所谓‘奠高山大川’,《尔雅》所谓‘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9]178所论甚确,即是指禹平定水患之后,继而划分疆域,为山川命名。“命名”在早期先民看来有着特殊意义,名与物是不可分的,名字具有神秘而巨大的力量,谁知道事物之名,谁就享有支配此名词所指之物的神秘力量⑤。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记载的是多种鬼怪的名字、形貌和驱除这些鬼怪的方术。知道鬼怪的名字,是驱鬼的一个基础。由此可知“命名”对于先民的重要性,禹因为有能力平定洪水、疏通河道,进而能够掌握给山川命名的能力,即对于山川有主宰能力,使得山川形势符合民众的需求,保障了民众的生存环境。此句强调的是其作为“人”所具有的能力与功绩,而非表达禹为山川之神的地位。
禹和伯夷、稷并列,同为“皇帝”所命,并称“三后”,可见三人的时代相当。《国语·郑语》云:“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10]469伯夷乃当时传说中姜姓之始祖,就如同周之后稷、夏之禹,是三族能追溯到切实可靠的最早的先祖。因此在这段叙事中,三者并列,都是承受天命,救民于困苦之中的人。且伯夷、禹、稷各自在制度、环境、农耕方面有开创之功,三人地位相当,并各为一族之始祖,并非高居天上的神灵。
此篇中“三后”均为人祖,承受天命,对于民众的生存延续有着莫大的功绩,由于初民不可能知道他们为何拥有这样的能力,故而归结为天命他们带来典常、嘉种,而承接这些天命的“三后”如同“文王”一样,是人而非神。因此《尝麦》中所论之“黄帝”“赤帝”二后同样是承受天命的“人”,而非神灵之属。
除了黄帝、炎帝以外,春秋时期称颂之“古帝”还有帝鸿、帝夷羿、帝喾、帝尧、帝舜数人。对于这些人王称帝的原因,前贤解释已较为清楚,即是作尊号比拟于天神上帝,故而以其功德卓著者称之为帝⑥。但需要补充的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期仅仅是萌芽而已。据统计,《国语》《左传》中除了黄帝、赤帝之外,以人的身份称帝者仅帝喾、帝舜、帝鸿、帝夷羿四人,商人之帝乙、帝辛之谓应当是沿袭商人本身称谓而来,与本节所论并无关系。其中帝舜2次,帝喾2次,余者1次。而单独称舜见于两书共6次,单独称喾者1次,后两者均未见。
但是在战国时期的众多文献中,“帝某”之称则迅速蓬勃起来:帝舜22次,帝尧19次,帝喾7次。可见在春秋时期,这种称谓并未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方式,也并没有真正形成《左传》所谓“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中以“帝”为王天下的称号之观念,卜偃说这句话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励晋文公出战,肯定贞卜的吉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在当时人追述的古史中“王天下”的禹、汤、文、武并未有过称“帝”的情况,可见在时人信史之中,并无君王以“人”的身份称帝。称帝者均为夏以前的传说人物,这种萌芽的出现,应当与下文所论普遍的祖先崇拜被赋予神界的职官、权能的现象有关。传说中的祖先,不仅仅死而为人鬼,在世时就具有神话色彩,这一过程,或可谓历史的神话化⑦。春秋时期还是人们整理传说、完善古史的时代,李锐先生即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炎黄为主体的多元系统,可以称为炎黄主体型古史系统。……其时代序列大体上是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11]。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古史人物被神化的程度也并不高,故而称“帝”的情况仍较为少见,直到战国文献中,大规模的神话与古帝王称谓才开始出现。
二、《左传》《国语》中“帝”的含义
记载春秋史事与言语的《左传》《国语》中单独称帝者共6例,其中4例可明确指天神上帝,余下较有争议的两则如下:
1.《国语·晋语八》子产称引古史“昔者鮌违帝命,殛之于羽山”[10]437。
由于《左传》昭公七年亦记此事,谓“昔尧殛鲧于羽山”,因此韦昭注等均以此“帝命”为“尧命”。但是《尚书·尧典》则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⑧。以诛杀鲧者为舜,非尧。《国语·周语下》亦云“尧用殛之于羽山”[10]94。韦昭注为弥合尧舜两说,故云:“尧时在位,而言有虞者,鲧之诛,舜之为也……舜臣尧,殛鲧于羽山。”如果以“帝”为人王的实指,则可有尧、舜两说,非必为“尧”。再者,《国语·周语下》周灵王太子晋在谏言治水意见时引共工、鲧的古史故事,指出他们就是雍塞治水,违背了皇天所主张的疏导,从而遭到皇天的惩处: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崈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这段传说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着更为神话的演绎:“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12]5034此中所述之“帝”无疑是作为天神之“帝”。故而《国语·晋语八》中所说“鲧违帝命”即是指鲧违背天道之意,而不是指他具体的违背了帝尧的命令等,至于诛杀鲧的人,则在不同的传说中有尧、舜、祝融等不同的表述。
2.《左传》昭公元年,郑伯遣子产探视晋平公疾病,叔向表示卜人占卜得知是实沈、台骀作祟,导致平公生病,但是晋国的史官对这两位神灵都不了解,故而求教于子产,子产详述了此二神的来历。实沈为高辛氏之子,与其兄阏伯不和,因此: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
“后帝”,杜预注:“后帝,尧也。臧,善也。”孔颖达《正义》曰:“襄九年传称阏伯为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尧也。”然而仔细分析这则神话的内容,应当可以看出,“帝”实际是指天神上帝。
这段故事讲述实沈原本为高辛氏之子,由于其被封于大夏,主参,故而其为参神,属日月星辰之神。理解这段内容的关键在于“主”字的含义。杜预注“主辰”为“主祀辰星”,则实沈由于“主祀参星”,然后成为了“参神”,也即是参星之神。实沈从祭祀参星的人,突然变成了参星之神,其中变化则未有叙述,反而是插入了一段叔虞封唐为晋侯,参为晋星的故事。在此段故事之后直接便说“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实沈就成了参星之神的名称。其中由人而至神的变化殊为突兀,难以理解。
然而对比下文关于台骀的来历,则或可解释实沈的变化。对于台骀的身份和神格,子产解释如下: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杜预注“玄冥,水官。师,长也,为官之长……业,纂昧之業”,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云:“业读为 。《方言》曰‘ ,续也’。”[13]1614即金天氏之子昧担任水官之长,台骀继承其父职事,继为水官之长。台骀担任水官之长时,疏通汾水、洮水,为台骀泽修筑堤防,从而使得汾水流域有宜居的高平之地⑨。由于他对于汾水流域有着如此重要的功绩,故而帝嘉奖于他,封之于汾川,使他的后嗣四国继续祭祀于他,他即是汾水之神。
这段论述中清晰地表明了台骀由水官之长转变为汾水之神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有功于汾川,他之于汾水流域,就如禹之于九州一般,为《国语·鲁语》展禽所论之“能御大灾则祀之”。他的后嗣祭祀他,亦不仅是将他作为祖先神进行祭祀,同时亦是将他作为汾水之神进行祭祀,也即如展禽所论共工之子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对山川的崇拜与对英雄祖先的崇拜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汾水之神具有了两种性质,一方面是自然的神性,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化身。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结合,也是宗教观念上普遍的状态⑩。由此对比,则实沈“主参”之“主”当训为“神”,《礼记·礼运》“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郑玄注:“社,土地之主也。”孔颖达疏:“主则神也。”[14]3071上引文中“今晋主汾而灭之”,主汾即为汾神。子产讲述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补充说明实沈的身份,因此这一段的主题应是论述实沈为何是参神。如果只是普通的主祀参星,并不能说明何以其为参神,故此“主”当为神。因其为参星之神,从而继续论述晋国因居于实沈旧居之大夏之事,表明晋景公会受参星影响,即是受到实沈的影响。
实沈应与台骀一样,都是始于人,而终于神,并且是以自然神灵的身份享受后人的祭祀。也正因此,子产将他们归为山川之神、星辰之神,而不再是人鬼之属。认为他们主管的是水旱疠疫、风霜雨雪等自然灾害,而不会造成晋景公的身体疾病。
在其由人变为神的过程中,尤其是成为自然神灵的过程中,“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即是由“帝”命实沈居大夏,主参星,亦是“帝”封台骀为汾神。此两次所云之“帝”并非旧注所云之帝尧、帝颛顼,应如其他4例一般指天神上帝。实沈与台骀由于得到天神上帝的册命,他们才成为了参神与汾神。
三、神灵官僚系统的形成
“帝”对于山川、星辰之神不仅有着统属之权,还有册命之能,此类自然神与“帝”之间形成了人间的君臣关系,由帝赐封任命,臣属于“帝”。
关于上帝对其他神灵的封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论及社稷五祀时所述较为详细: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杜预注:“五官之君长能修其业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为王者所尊奉。”孔颖达《正义》则云:“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虽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与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为配者神名。犹社本土神之名,稷本谷神之名,配者亦得称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礼使祀焉,是为王者所尊奉也。”此说均以为受封之五官因死后配食于五行之神,故而称五行之神的名字。然而,从先儒讨论社稷与人鬼的问题中可以看出,此祀为贵神,即是其本身成为贵神之意。如《礼记·祭法》亦云:
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孔颖达《正义》“祀以为稷者,谓农及弃皆祀之以配稷之神”,此“配”后儒多理解为配享之意。然“配”亦可理解为辅作、暂作之意11。许慎《五经异义》亦云:“今《孝经说》‘稷者,五谷之长,谷众多,不可遍敬,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说‘烈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为稷,稷是田正。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许君谨按‘礼缘生及死’,故社稷人祀之,即祭稷谷,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义。”[15]43贾逵、马融皆从之,应劭《风俗通义》、王肃《圣证论》亦从其说。此说即是以烈山氏之子柱、后稷均为稷神12。因此许、郑、应均以为句龙由后土而任社神,柱、弃则由田正而任稷神。
后儒往往强行割裂人鬼和地示之间的联系,如《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孔颖达《正义》即云:“故贾逵、马融、王肃之徒,以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认为地示不能为人鬼,故而以配享来理解此种“祀以为社”“祀以为稷”的内涵,实际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如王肃所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传云‘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龙也。”[14]3139即土正句龙与社即为一人,柱、弃也均作为稷神受到祭祀,都是兼有祖先、自然崇拜两种性质,故而涵盖了人鬼和地示两类,并不能勉强分开。
明确了句龙以土正之身份任社神,柱、弃也由田正而成为稷神之后,五官之神的设立便较好理解了。他们虽然均具有人的身份,但死后则祀为贵神,兼有了五行之神的身份。然而不同于司土、农正这样的职官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职官,五行之官于春秋的实际官制中并无可以比照者,此种官职纯粹是出于当时人的想象,认为存在掌管五材之官员,具有掌管金木水火土五材之权能,则知其从开始便具有神灵的属性。但是却还要声明其“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以此使他们具有享受大神祭祀的身份和地位。而赐封他们为上公的主语,即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论及豢龙氏时所述之“帝”:
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
此段中关键在于“帝赐之姓曰董”中之“帝”的指代,杜预等均无训,然《论衡·龙虚篇》作“而赐之姓”,这应是此后一种普遍理解,即以“帝”为帝舜之省称,如《孟子·尽心下》“姓所同也”,焦循注则云:“董父舜赐姓曰董。”[16]1024然而对比上下文,此“帝”未必是“帝舜”之省称。下文屡屡称“帝”,“扰于有帝”,杜注“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其德能顺于天”,以“帝”为“天神上帝”也。且此帝于孔甲时赐其乘龙,去帝舜之世已远,不可能是“帝舜”。而且前文所称“帝”如果即为“帝舜”,似不必复言帝,因此前文所称之“帝”,也应是指“上帝”。上帝嘉勉董父能够畜龙以服事帝舜,故而赐姓为“董”,此赐姓之谓,即如《国语·周语下》所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10]96之类。因此五官之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的主语应与此处赐姓董父的主语一致,均为“天神上帝”,而非舜或少皞氏。
“赐姓”问题,陈絜先生曾指出是周初特有的制度,与周初封建密切相关,强调受赐者的义务,是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行为[17]253。此时上帝对于五官之神的赐封,则是时人想象中以人世“列受氏姓”的意义比附于“上帝”及其臣属的关系,以此标志着这些神灵承担了“上帝”对其的任命,具有了比于上公,为大神的地位。“封为上公”即是指其在“帝”下属臣子中的地位较高,比于“上公”13。故而“列受氏姓”实际上标志的是其在神灵中官僚系统地位的确立,此后不同的传说英雄祖先任此神职,从人鬼进而成为“帝”下属臣子的一位。明确了这种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的情况,此种兼具人鬼与地示的现象便可以理解了14。
上帝之臣属并不局限于上述神灵之中,其余多称作司某或某师,春秋时期便有“司慎”“司盟”“司寒”,《周礼》中还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司民”“司禄”。
此时天神不再是基于其本身形象定义的自然神灵,而是基于其职事表述的职能神,虽本于自然之星辰,但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神,是具有某种特别属性、功能的自然物。如毕星司风,故为风师,箕星司雨,故为雨师。
这些称谓显然是基于人间的官称比拟而来,象征的也即是神灵中的官职,并非确切的某位神灵,不同的自然神灵或祖先神均可充任这些职位。其中周人自己重要的祖先后稷充任稷神,共工氏之子句龙兼任后土与社神。上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论及社稷五祀时云:
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14]4613
即云夏以前祭祀的稷神是烈山氏之子“柱”,商以后所祭祀的则变成了后稷,由此可知稷神与祖先神之间的联系并不固定,在不同时期会由不同的祖先任职。这套体系极似人间职官体系。社稷五祀均为神灵中的职官,名分虽定,但是任职之人不同时代有所差异。
由此可以总结,在春秋时期,人们以现实官僚制度为蓝本,构拟出了以上帝为君的职官体系。“上帝”为君,下辖众多以先祖身份任职的自然神灵,各司其职。故《礼记·月令》称有“帝之大臣、天之神祇”[14]2996,这些臣子均需要服从“上帝”的差遣和安排。
明确了祖先神与职能神的关系后,则可进一步考察“帝”称的变化缘由,自西周中晚期开始,得以随侍上帝左右的祖先神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周初的太王、王季、文王,至秦人所说秦人十二位逝去的先公都在上帝之侧。至战国时,上帝所在的帝廷之中挤满了不同族群的各位先公先王,依照人间朝廷的想象,这些帝廷中的神灵彼此自然也需要排定等级次序,曾经得以“王天下”的先祖无疑较之于其他祖先神具有更高的地位,为了表示这种等级上的差异,则将这些先祖称之为“帝”,以此凸显其高于其他祖先的地位。
《吕氏春秋》记载的五帝,高诱注均解释为“讬祀”,如
“其帝炎帝”,注云“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死讬祀于南方,为火德之帝。”[18]83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注云“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轩辕氏,死,讬祀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龙能平九土,死,讬祀为后土之神。”[18]133
“其神蓐收”,注云“少皞氏裔子曰该,皆有金德,死讬祀为金神。”[18]154
从高诱的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五行之主,还是五方之帝,均是作为人的祖先死后“讬祀”,“讬”,《说文》云“寄也”,《论语·泰伯》“可以讬六尺之孤”,邢昺疏云:“谓可委托以幼少之君也。”[14]5401讬祀并不一定理解为配享,亦可以理解为委任、祀为之意,即是黄帝、炎帝、后土、该等死后祀为天帝、后土之神、金神。也即是这些祖先去世后在神灵世界中担任这些职官,成为相应的职能神,天帝亦为此类职官。
《逸周书·太子晋》亦云:
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曰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15
太子晋论及士、伯、公、侯、君乃至天王的称谓条件各有标准,均非生而贵者,乃其德行合于相应的标准,掌握相对权责而得称之。论述中均云“曰”或“谓之”,王念孙云“曰与谓之同义……言曰则不言谓之”。“曰”与“谓之”代表的就是在世时对其的称呼。然而到了“帝”则不再延续这一固定辞例,转而云“登为帝”,“登”即升也,参照下文王子晋自云“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则此登即应是去世后升入帝所而成为天帝之意16。
《吕氏春秋·古乐》亦有类似记载,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高诱注:“惟天之合,德与天合。”[18]123此说与上引类似,亦是以帝颛顼处居空桑,后因其德与天合,教化八方,故能升为天帝。
从而可知当时人认为天王中能德合天地,使四荒臣服无有怨怼者,则去世后便会在神灵世界中充任帝职,加以“帝”之尊号。也即是说祖先神中曾任天子且能使四荒臣服者便超越其他充任社、后土、金神一类的祖先,成为天帝。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人生死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神灵与人间仍彼此相通,去世的祖先在天上仍有职官更迭,掌管着人间的事务。可以说这一过程即是将祖先神与帝廷中的职官融合的进一步表现。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所云“今之王,古之帝也”[14]3951。便已经开始提出“帝”是与“王”类似的官称,只是将其归结为古今之差别。实际上则是天神中之君长称为“帝”,人间的君长称为“王”,而去世的祖先担任神灵官僚体系中的不同职位,其中最为重要的便可以充任“上帝”一职。同于人间君王的时代更迭,天上之“帝”亦代际交替,由此便有了“群帝”这样的群体。如《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18]320《山海经》中更屡屡提及“群帝”,如《大荒北经》云:“乃以为池,群帝是因以为台。”郝懿行案:“即帝尧、帝喾等台也。”[12]5012-5013其后又因配合五行,故而往往以五为数作为指称,故而不同的论述中则从这些被视为“帝”的祖先中挑选五位构成“五帝”,这种“五帝”的组成则有一定的随机性,并不固定。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帝”从卜辞中抽象、模糊的神灵逐渐被虚化,成为一个由祖先神担任的职位。“上帝”从笼统的天神之尊长,成为所有神灵的君主。同时,时人对神灵的认识从崇拜基于本体的自然神开始转向基于权能的职能神。基于此观念,“帝”亦成为神灵的“官称”,去世的先祖充任帝廷中的各类职官的同时,格外受到尊崇的先祖则开始担任“帝”之一职,故而被称为“帝某”。人们以现实官僚制度为蓝本,构拟出了以上帝为君的职官体系。“上帝”为君,下辖众多以先祖身份任职的自然神灵,各司其职。故《礼记·月令》称有“帝之大臣、天之神祇”,这些臣子均需要服从“上帝”的差遣和安排。故而由此出现了一批可以被尊称为“帝”的祖先,在文献中亦以人的形象出现,应因不同的需要会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包括了四帝、五帝、六帝等说法,具体所指的祖先亦有不同。这些古帝王间则被构拟出世代相袭的血缘关系。
注释
①徐旭生先生曾指出:“专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们那半神半人的性质。帝就是神,单称‘帝’或加一字作‘皇帝’,而下面不系专名的,均指天神,并无真实的人格……可帝下带着专名的却是指的人神,他们虽说‘神’气十足,而人格却并非子虚。必须兼这两种性质来看,才近真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顾颉刚先生认为:“帝号的作为职位和称谓始于秦。”(此说之帝号指人王所用之帝号。)顾颉刚:《致胡适: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原载《古史辨》(第一册),后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第4页。亦有许多学者认为“人帝”之称是战国时人的想象,始于齐秦互帝。如裘锡圭先生认为:“到战国时代,随着传说中天帝的人王化,地上的统治者也开始作称帝的尝试,但直到秦始皇才真正把这个企图实现。”裘锡圭《读书札记九则》云“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原载《文史》第15辑,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第395页。②赤帝,李学勤先生认为即是炎帝之误,赤、炎二字字形相近,见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第91页。③“大常”今本原作“大帝”,此据朱骏声意见改,详见《逸周书·尝麦解》,第734页。④下文说明命少昊为鸟师,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其少昊明确为人名,因此此处“于宇”宜从陈逢衡训为往、隶,即隶属其下以佐少昊之意。⑤此种命名的力量被弗雷泽称为“名字巫术”,他指出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危害于人。(参见弗雷泽《金枝》,第400页。)⑥这种帝称的来源,刘复先生认为乃是后世对确曾存在过或虚构的先王不断神化的产物(刘复:《“帝”与“天”》,顾颉刚编《古史辨(二)》,第22-23页)。卫聚贤先生认为因“帝”本为至上神主宰人类的一切,“古有圣德统一的共主可称帝”,盖“帝”有高于“王”之意(卫聚贤:《三皇与五帝》,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三集)》,第144页)。郭沬若先生认为“帝”为宇宙之真宰,“人王乃天帝替代,因而帝号遂通摄天人矣”(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沬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54页)。徐旭生先生曾指出“专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们那半神半人的性质。帝就是神,单称‘帝’或加一字作‘皇帝’,而下面不系专名的,均指天神,并无真实的人格。可帝下却是指的人神,他们虽说‘神’气十足,而人格却并非子虚。必须兼这两种性质来看,才近真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⑦关于历史神话化,一般的认识是:“所谓历史神话化是指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始祖和其他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赵沛霖:《论奴隶制时代历史神话化思潮》,《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第119-124页)或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历史上的人物经过神化而有神性,其事迹经过夸张而变得非凡”(王青:《中国神话形成的主要途径:历史神话化》,《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第47-51页)。⑧《尚书正义》卷3《舜典》,第270页。(《今文尚书》中附于《尧典》内。)⑨“太原”,杜预注:“晋阳也,台骀之所居。”杨伯峻则以为此非地名,乃汾水流域高平之地,此说较为合适。⑩如前述卜辞中河和岳即兼有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双重属性,是两种崇拜结合的表现。民族志资料中亦有体现,云南路南彝族的“密支”神也是社神祖先化的典型实例,据当地彝语,“密”为土地,“支”为祭祀,所谓密支就是社祭。然而在密支节祭祀仪式上,所请的主神,却是“普”“楠”二神,即男祖先和女祖先(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第418页)。11《诗经·小雅·甫田》“以介我稷黍”句,孔颖达《正义》引《郑志》中郑玄答赵商问后土祭谁,社祭谁,云:“后土为社,谓辅作社神……句龙本后土,后迁之为社。大封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龙为后土,后转为社,故世人谓社为后土,无可怪也。”此论中郑玄详细解释了句龙转化为社的过程,即其本为人,担任土官一职,死后则成为社神,享受社神的祭礼。辅作社神,即是以后土作为社神之意,而非配享之谓,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孔颖达正义引《郑志》中郑玄答赵商云:“《左氏》下言后土为社,谓暂作后土,无有代者。”辅作与暂作类似,即是社神之职位暂由后土任之,并非如孔颖达所解释:“句龙职主上地,故谓其官为后土。此人为后土之官,后转以配社,又谓社为后土。”谓配享之义。故而考之上引郑注“祀以为稷者,谓农及弃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中所言之配,亦未必是配享之意,而应是农、弃以人鬼暂作稷神之意。12稷神的内涵当如金鹗《求古录礼说》“社稷”条中所云:.社字从土,明是土神。稷字从禾,明是谷神。13孔颖达《正义》引王肃云:“春秋说伐鼓于社,责上公,不云责地祇,明社是上公也。”王肃即提出春秋传以为“社为上公”,可知“上公”可以借以形容神灵。14这种现象在神话的发展过程中亦十分常见,赵沛霖根据卡西尔《人论》,总结出希腊神话中神灵形象的发展,他认为:希腊神话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功能性诸神阶段。所谓功能性诸神就是主管某种自然现象和某些活动的诸神,如司雷电、风雨之神,司采集、狩猎之神等等。与上一阶段面貌模糊的原始诸神相比,它克服了模糊性,而具有了一定的具体性。但是,这种具体性还仅仅是“表现在它们的行为上,而不是表现在它们的人格化的外表或存在上”。它们因此也就没有专名,如宙斯、阿波罗等等,更没有个性,而只有表示功能与活动的名称,因此也就只能靠功能和职责区分他们(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对比希腊神话的神灵形象逐步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所述的这些神灵,已经经历了以自然物为本阶段,但是在具有人格化的过程中,则是通过与历史上的英雄祖先相结合,从而具有了鲜活的面貌、性格和个性。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历史与神话互相渗透的结果。15《逸周书》卷9《太子晋》,第1023页。16《王子晋》一篇陈逢衡云“其为战国时文无疑。盖其事与谏壅榖洛同在周策,《国语》既得其精,而《逸周书》拾其粗也。故《潜夫》述之,《风俗通》亦述之。”此论甚确,王子晋虽为灵王子,然此篇论事已及晋亡及孔子,当在其后,因此这篇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帝”观念[J].中国史研究,2016(2):43-61.
[2]李明阳.论春秋天神崇拜中的帝[J].亚洲研究,2017(21):93-126.
[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李学勤.《尝麦》篇研究[M]//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7]张怀通.《尝麦》新研[J].社会科学战线,2008(3):106-115.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戴钧衡.书传补商[M]//续修四库全书(第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李锐.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9-114.
[12]郭璞传,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M].济南:齐鲁书社,2010.
[13]竹添光鸿.左氏会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8.
[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陈寿祺撰,王丰先点校.五经异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6]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8]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