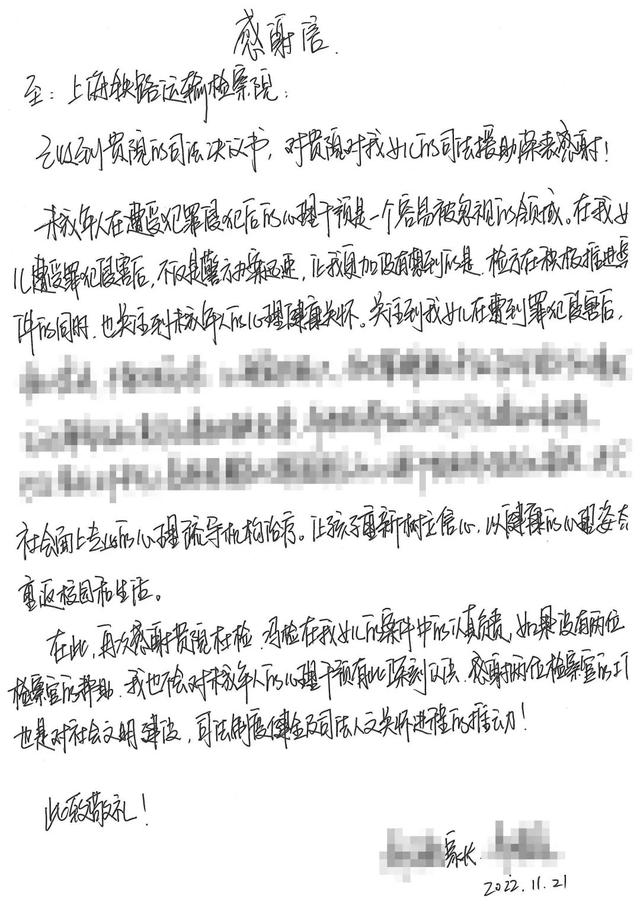王学泰(中)与学者们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

王学泰 (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北京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中国流民》《水浒与江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郑雷
2018年1月12日清早,寒气逼人,我正准备起床去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的一个新书发布活动,忽然接到管小敏老师发来的短信:“学泰今早走了,回去天国上帝的怀抱。”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实在难以相信,我立即回拨电话,证实了消息确凿无误,一时心神恍惚,不由靠在床头愣怔了半天。蓦然想起2016年1月,也是这样的天气,我意外得到原《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褚钰泉先生去世的消息,给王先生打电话:“您知道褚先生的事吗?他走了。”王先生问:“哪个褚先生?”我说:“是褚钰泉先生。”王先生当即叫了一声:“哎哟!”就这一声,隔着电话,我清清楚楚听到他心底的疼痛。没想到两年之后,他也以这样的方式将疼痛永远地留给了我们。
不纯然是书斋里的学者
他惯于也善于将书本与现实相融贯
认识王先生算来已在十年以上,但彼此真正熟悉却还是近几年。十几年前,一次去拜访蓝英年先生,在客厅见到几册别人送他的书,随手打开最上面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扉页有作者的题字,后面留着签名“学泰”。据蓝先生介绍,王学泰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从游民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富于创见,在学界影响很大。其后我不止一次听蓝先生夸赞王先生的淹博和睿智,最爱举的例子是:“吃饭要有学泰在,不用担心冷清,他一个人就能包场了。”不久我应江苏一家报纸的请托代组名家稿件,通过几位熟悉的先生辗转约请了一批作者,其中就包括王先生。某次参加一个小型宴会,跟王先生碰了面,散席出来时,他顺带问起约稿的事,我简要说明情况,彼此匆匆而别。后来又一起开过几次会,都不及深谈。
真正见识王先生的风采,还是在2007年初春的一次餐叙上。饭局约在南城,我随林冠夫、林东海两位先生赶到时,早已高朋满座,同席十几人中,我认识的有邵燕祥、蓝英年、朱正、陈四益等先生,王学泰先生也在其中。大家庄谐并作,随意谈论着各种新闻与学林掌故。饮宴过半,王先生兴致高涨,言谈渐入佳境,说起他正在读的恽毓鼎日记,特别提到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轿子过河时需加拆卸之类今世早已陌生的风习。话题一转,又谈到1949年后大陆各地出现的多起“民间称帝”事件,剖析民间社会的特性,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研究游民文化的心得了。一走神间,王先生又换了话题,转头细听,似乎是在慨叹时人读书的粗疏,说曾见有文章提及古代搜求民间遗佚文籍,征集上来别有奖赏,“还给点儿吃的”。他觉得不可思议,翻出原文来一看,是“付之梨枣”。一言既出,同席者无不莞尔。古代常以梨树和枣树的木材为雕版材料,“付之梨枣”正是交付出版之意,哪是给什么吃的。
后来不止一次与王先生同席,时常领略他的妙语。王先生正如前人所形容的,“于书无所不窥”,只要绣口一开,便滔滔汩汩,茫无涯涘,欬唾珠玑,随风抛掷,亹亹清言令人忘倦。有事向他请教,往往是问一答十,来者不拒,就像《刘三姐》里唱的:“你拿竹篙我拿桨,随你撑到哪条河。”他的渊博、智慧,他的深刻、精警,他的爽朗、宽宏,连同他不时流露的幽默,都在里面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谈话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不外两种情况。一是高屋建瓴,对书本内在精神的把握较常人更为准确和深刻;二是阅历丰富,通晓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两种才能,王先生都具备。他命运坎坷,有过劳教和监狱服刑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对社会有着深细的观察和真切的认识,加之记忆力超强,口才又好,所以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不单引经据典,而且现身说法,令人由衷信服。王先生不纯然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惯于也善于将书本与现实相融贯,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蓝英年先生曾戏言王先生是иметь вес(俄语),意即“有分量的人物”,他解释说,这个俄语词组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身体壮硕沉重,一是指有水平有地位。
他说得没错,无论从哪方面看,王先生都是一种伟岸的存在,跟他同行,稍微落后一点,就会为他的影子所笼罩。
只要稍有闲暇
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开示
2014年,供职于出版社的张杰先生打算为一些文化名家出专集,拟定的名单中也列入了王学泰先生。因为跟王先生不熟,托我求陈四益先生代为约请,定好在崇文门国瑞城的西湖汇餐厅见面。那天王先生带来几本刚出版的《监狱琐记》,签赠每人一册。听张杰讲明意图,王先生很高兴,表示支持。其后张杰命我赞襄有关出版事宜,与王先生的联系因此逐渐多了起来。
不久南京董宁文先生来北京,他主编的民间读书刊物《开卷》出版将满十五周年,计划2015年春夏之际在南京召开座谈会。蓝英年、王得后、王学泰等先生都受邀参加,临期蓝英年、王得后先生因事不克赴会,王学泰先生带着夫人管小敏老师和陈四益、郭启宏等先生一起到了南京。或许是很久没见到这么多同道了,王先生难免有点兴奋,每天清晨即起,到附近散步,然后在早餐厅边进食边与来自各方的朋友交谈,神情愉快而满足。会议在一处露天庭院里举行,王先生与董健、俞律等先生同桌,彼此倾慕,畅聊了一下午。
返程时山东画家郭睿先生要我请王先生夫妇到济南盘桓,我陪同他们游览了大明湖、趵突泉,一路上王先生兴致盎然,不停地说着话,谈李清照,谈聂绀弩,谈冯友兰与章廷谦,甚至还在进餐时跟郭睿谈起了站桩的几种方法。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正在构思的《中国笑话史》,我问他如何评价邯郸淳的《笑林》和侯白的《启颜录》,他说魏晋至隋唐五代是笑话的自觉时代,这两部书在笑话发展过程中都有开创之功。按他的构想,西周至春秋可定为笑话的萌芽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则是笑话的附庸时期,但这两个阶段可用材料不多,大概仍以先秦诸子和《史》《汉》等内容为主。经过六朝和唐宋的发展,中国笑话直至明清才进入繁盛期。说得高兴,他信口讲起《笑林广记》等书中的笑话,我恰好读过,顺着他的话说下去,王先生开心地笑了。
因为南京和山东之行,我跟王先生进一步熟识起来。或许是觉得孺子可教,每次打电话去问安或联系别的事务,王先生只要稍有闲暇,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开示,最长的一次将近三小时。就在这种长时间的通话中,我体会了他的热情,也感知了他的寂寞。由此形成经验,每次跟王先生通话,总是先安排好一切事情,然后正襟危坐,开始拨号,准备着随他共入书山学海的逍遥之境。
2015年5月,几位画家朋友在北京建立工作室,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之意,定名虚白馆。我衔命草成短文《虚白解》,特地呈送王先生邮箱,希望他过目后能提点意见。第二天晚上即收到回信,其中专门谈及对“虚室生白”的独特理解:“过去我读庄子,至‘虚室生白’处,常常联想到小时候曾住过庙,我们住在偏殿,屋子大,家具少,纸窗破碎,每到夕阳余照,一缕缕阳光射入空阔屋子里,一束光柱,洒在地面,原来僵硬黑土的地面显示些光亮出来,那光柱中则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容得万类飞舞;我想先秦的屋子更是这样,‘绳枢瓮牖’,到了春夏,瓮去,窗子就是一个空洞,既无纸糊,更乏绢帛,屋子像一个没牙的老人,‘虚室生白’或给庄生更强烈的印象。以佛释庄,早年读关锋文章多引宣颖《南华经解》,一直想找来看看,拖至现在也没看过。真是人间多有未读书。一笑。”读罢这段话,我眼前立时浮现一个形象的场景,庄子贯穿数千年艺术史的名言顿然在心头活了起来。以生活阅历解经,正是王先生好学深思、不拘故常的生动体现。
日常生活中
王先生的善良更多体现为应世谐俗
我与王先生的很多信连同王先生的书一起反复读了多遍,深觉他的学问与性灵乃至人格早已融冶为一,写出的每个字都是心血浇灌而成。不少人一接触王先生,往往不自禁地为他的智慧所倾倒。相处久了,才会发现他宽厚豁达、善良淳朴的另一面,我觉得这应当是王先生更为本质的特征。
2015年岁末,应江苏如皋水绘园之邀,我陪同王先生前往讲学。招待的宴席上,水绘园管理处主任陈祥云先生讲起在拆迁办工作的经历,说自己如何耐心做群众工作,平息闹事者的怒气,又如何尽力保护老人和弱者,赢得一些拆迁户的敬重。因为事例都来自实际生活,他讲得又很诚恳,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了。这时水绘园的徐小维老师忽然惊呼了一声:“王先生,您怎么了?”循声望去,王先生正用手擦着眼睛,或许是被讲述中流露的善良所感动,或许是哀怜民生之多艰,他情难自已地流下了泪水。
我联想到王先生《〈百年一遇〉序》里的一段话:“我几乎是流着泪,把这本书的打印稿读了一遍,特别是书中写到六六年‘红八月’那一节……当我们现在轻轻松松侈谈‘爱’的时候(当然有必要谈),不要忘记那个互相猜忌、互相恨的时代。”面对苍生的苦难,王先生保持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悲悯情怀,眼中流泪,心中流血,他的不少煌煌大文都像这样经过了血泪的浸泡。
日常生活中,王先生的善良更多体现为应世谐俗。管老师因为生过一场大病,日常以素食养生,为照顾她的习惯,王先生也随着素食多年。但每次与朋友相聚,他不愿扫大家的兴,虽不饮酒,倒也荤素不忌。每次与张杰去王先生家,管老师总是客气地留饭,而王先生的客气是不留饭。他知道张杰不爱吃素,不愿勉强他,常会说一句:“我也不留你们了,你们出去吃,可以自在点儿。”这就超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做到了“己之所欲,亦未必施于人”,体贴人情之周到为他人所不及。
听管老师说,最后住院期间,王先生还在病床上口述了多首留赠亲友的诗。写给管老师的一首七绝中有“多情最是堕泪处,老来夫妻携手情”之句,心中的留恋和凄苦不难想见。几天后他又为女儿写下一首诗:“吾儿初生时,处处牵我手。纵横床上滚,竞游室外走。或怒或欢愉,扬起小嫩手。父手已鸡皮,儿手玉连肘。今年忽多病,吾儿已焦首。劝儿好心态,共享百年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一颗慈父的心呢?但王先生似乎觉得话还没说透,管老师告诉我,他住进重症监护室以后还想修改,最终也没改成。
在长文《大儒杜甫》中,王先生以浓重的笔墨热情赞美了这位千古诗圣,认为杜甫“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但“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
王先生眼中的杜甫“还能体现儒家近于人情的风格”,对妻儿有爱,对朋友有情,甚至于对“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都充满了关切,“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惟仁者能知仁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王先生自己的写照。
他宁可在报纸开专栏,也不肯花一点心思气力去争课题费
也许是王先生的淹博、宽厚给人印象太深了,大家鲜少注意他还有清高狷介的一面。王先生所在的社科院是国家级学术机构,常要承担某些特殊任务,给领导讲课就是其中一项。
有一次指定王先生去讲“扬州八怪”,有关部门通知下来,要求正式讲课前先试讲一次。不知是不是觉得这样对讲课者不够尊重和信任,王先生很坚定地表示,如果要试讲,就不去了。有关方面经过研究,同意他免除这个环节,直接给领导讲课。事后有人问起,他只简单地略述经过,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去大学课堂作了一次普通的讲座。
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了半辈子,王先生从没想过借助单位的优势为自己争取什么利益,用他最后在病榻上口述的诗句说,是“在所三十年,不争芋栗半”。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他宁可在报纸开专栏,不分日夜地写作,也不肯花一点心思气力去争课题费。
2017年7月27日,张杰带了两位出版社的编辑去找王先生商量出版合同,顺带约我一道去看望。见面发现王先生瘦了许多,精神倒还健旺。他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正在恢复期间。王先生告诉我们,术后需要加强营养,所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每天都适当吃一点肉。然后正式研究他作品系列的出版事宜,慢慢引申开来,谈到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王先生若有所思的面容和深沉凝重的话语。告别出来,我想起他文章中引用过的一联杜诗:“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心下黯然。不想这竟是与王先生最后一次的正式见面。
接下来的几个月忙着各种杂事,没顾上去看王先生,一半也是怕干扰他静养,只是请人在如皋代购了些肉松之类土特产寄给他。一个晚上接到王先生电话,说是在住院观察,此前几次打电话来,都没人接。我赶紧致歉,说明原因,不是在单位忙,就是因公出差,较少在家。话筒里王先生的声音清晰而稳定,似乎状况还不错。
虽然身在病房,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将近一小时,我理解他住院的孤寂,却又唯恐影响他休息,提醒了两次,约好等他出院到他农光里的家中相见,才结束通话。过几天再问,说是医生暂时还不让出院。于是周末约了郭睿等朋友同去探视,到达时已近中午,王先生刚好睡着,病容满面,颇显憔悴,我心中凛然一惊。
离开医院不久,王先生醒了,特地打电话来道谢,我听他声音疲惫,没敢多说,劝他注意休息,早点出院,就匆匆挂断了,心头涌上一丝伤感,隐隐觉得不安。12月26日上午管老师以短信告知:“学泰现在住在ICU,昨天凌晨2点突发急性心衰,大夫不顾我的不同意伤害性抢救的签字,毅然插了管,生命算是抢救过来了。大夫说要不五到十分钟内人就走了。感恩!一切交给上天吧。”
我惊愕无语,因为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两年前我陪他参访南通时,在一个朋友家,他为了显示力气,一只手就提起了一张几十斤重的硬木雕花椅,所以这一次,我坚信他一定能闯过难关,回到我们身边。然而,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意外地猝不及防地落空了。
王先生离世已经一年,不再有人打电话来海阔天空地长谈。望着无声无息的座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想起苏东坡的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懊恼自己错过了太多宝贵的学习机会。虽然杂事繁多,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自己太过懒散,没能抓紧时间多向王先生请益,聆听他口中的种种要言妙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先生在文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广为人知,尤其是他围绕“游民文化”展开的系列研究,为人们观察与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新异的视角和思路,被称为当代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天假以年,他必能为世间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先生的离去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我个人的遗憾实微不足道。
一次电话闲聊,谈到许多传统事物的消逝,王先生说汪曾祺先生一篇作品的结尾说得好,有些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这话他来回重复了几遍,我感觉他说时是在无奈地苦笑。过往的良风淳俗,种种美好的人事,包括王先生这样不可多得的文化大家,真是“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吗?王先生已去,我无法再向他请教。
供图/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