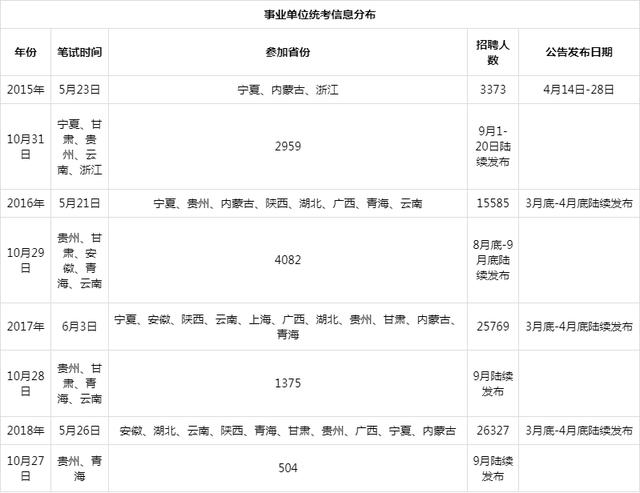原创:刘起来

骑兵驯马的主要任务是调教新马,使人能够骑乘。另外,就是对战马进行一些特殊驯练,使马的功能达到全面有效发挥。在我当骑兵的五年中,曾亲自调教驯服过两匹烈马,使他们成为人见人爱的骏马,还进行了训马卧倒和走马训练。
我调教外蒙古“小花马”骑兵部队为做好战马的新老更替,一两年就要接回来一批新马服役。西北军马的主要来源是甘肃省的山丹军马场,这里地处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盛产良马。据传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当然,偶尔也有其它来源。比如1965年我团就接回一批外蒙古马,听说是抵账来的。但不管是哪个地方接来的马,都是两三岁的口青马。这些马在离开养马场前,不但人没骑过,有的可能连人都没见过,比如外蒙古马就是这样。
据接马的战士回来说,蒙古人养马很多,都是分群围栏放养,平时极少见人,也没喂过精饲料。往回接时,不是一匹一匹抓住赶上车往回拉,而是在牧场边,开出一个通道铺上铁轨,火车皮倒着开进去,马是由人驱赶进入车厢的。这些马野性十足,见人视如仇敌,刚进营区连笼头都戴不上,备鞍子就更不要说了。有的马,人一接近还给人示威,个别烈马还踢咬人。所以说马不经驯服,根本无法骑乘。
骑兵部队没有专门的驯马师,新马一来就分到了班,由各班组织调教。驯马的办法是根据马的具体情况,一般有三种。一是不让戴笼头的,就用长绳绊倒,几人压住强行戴上;二是备不上鞍子的,就拉入钉掌的架子内控制起来,备上轻乘鞍子,这种鞍子是专门用来驯马的,前鞍桥铸有铁环便于手抓;三是对于不让骑或骑上就尥蹶子的,先装上两麻袋各约重一百斤的沙子,系在一起抬上马背,一人骑马在前面牵引,另一人骑马在后面驱赶;待新马跑的精疲力竭时,卸下麻袋人再骑上。对于多数新马来说,调教上十天半月就让人骑了。但对个别烈性马来说,十天半月还远远不够,还得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调教。

我曾训过两匹烈马,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感受颇深。训的第一匹就是外蒙古马,此马个头不很高,但有骏马的体貌,长得特别精神,毛色淡红,油光发亮,额头长着一坨白毛,两胛附近也各长一坨很对称的白毛,甚至四蹄蹄腕长的毛也是白的,显得很特别,所以都昵称它为“小花马”。这匹马刚接来就分到了连部,准备让通信员骑乘,可没想到的是小花马性子很烈,连部的人试训了几次,连鞍子都没备上过,勉强给戴上了笼头就放弃了调教。
我于1966年7月由五班副班长调任十二班班长.这个班是刚组建的四零火箭筒班,马是从各班抽调来的,质量确实有点差。我作为一班之长骑得是一匹个头不高的老马,虽有几步小走,骑上还挺舒服,但奔跑速度太慢,心里总觉得不如意,所以就惦记起小花马来,请求副连长把小花马换给我们班,副连长爽快地说:“换什么,拉走就行了。”我们把马拉回拴到马场,我手捧马料往小花马嘴边递,试图接触一下,可它耳朵一抿,鼻吐粗气,头往上一扬,前蹄做出扑人的动作。
我一看此马果真不是等闲之辈,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第二天(星期天)我和副班长周祥祖(我的同乡)带着两个新兵来到马场,我俩一人抓笼头,一人给戴嚼口,可小花马不停地摆头,前蹄也不停地乱刨,我看无法戴上,就让两个新兵取来一根长绳,把小花马拉出马场将其绊倒,捆住四蹄强行往上戴,可就是不张口。这时我突然想起学骑马的第一课,老班长讲的窍门,即将食指从嘴角插入到智齿部位的无牙处,我一试还真灵,小花马乖乖地张开了嘴。戴上嚼口后,我们解开了绳索,小花马一跃而起不停地活蹦乱跳,我用力拉了两下嚼口带,好像感觉到疼了,才停了下来,但仍惶惶不安。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试着备鞍子,可小花马左躲右闪,鞍子无法搭到背上,只好拉入钉掌的架子里,四面用绳围起,才把轻乘鞍子备上。然后又将备好的两麻袋沙子抬到马背上,拉出架子后小花马又想尥蹶子,但身上驮着重物没有尥得起来,拉它走它又不走,后面驱赶才肯前进。我觉得这匹马的野性太大,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先磨掉它的野性,消除对人的敌意。所以就将小花马拉到教练场,先没有往上骑,而是我和周副班长都骑上自己的马,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驱赶,先是慢跑后是快跑,大约跑了有40分钟时间,小花马大汗淋漓,好像累的走不动了,我们才下马休息。
趁此机会,我接近小花马,它没有过激反应,便从裤兜里掏出马料,放进帽壳(担心咬手)递到嘴边,说也奇怪,它对我没有表示出敌意,竟然戴着嚼口吃了起来。这时我又用另一只手,搔摸它的额头(以后一接触,都有这个动作),轻拍了几下脖子,可能是觉得舒服,站着没动接受了我对它的示好。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操练了约一个小时,结束了第一天的调教。
从第二次调教开始,把麻袋的沙子减少了一些,我在别人的帮助下试骑了一次小花马,可一上马它就开始尥蹶子,只因背上的负荷太重,蹶子尥的不高,我又有铁环辅助,没有把我摔下来。就这样,又骑训了近半个月,我以为小花马该老实了,第一次卸掉麻袋,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上了马,可牵引着没走几步,突然尥了一个很高的蹶子,把我摔了下来。好在教练场的地面全是沙土没有受伤。无奈,又把沙袋抬上马背骑了上去,也再没尥蹶子。从此以后小花马有一大进步是再不需人牵引,能自觉跟着其它马走。

就这样又调教了一个多月以后,再次卸掉装有沙子的麻袋,由副班长抓着笼头我上了马,不过这次我的警惕性很高,双手抓铁环,两腿把马背夹得很紧。同时,在上马前我就给前面的人讲:“我一跨上马背,你们就加速。”因为马的群体意识很强,小花马看到前面的马都奔驰而去,也没顾得上尥蹶子就跟着奔跑起来,奔跑了有四五公里后,我们下了马休息,在溜马期间我又给小花马施以小惠,并不停地摸它的额头,以示友善与鼓励,这时我觉得小花马温顺了不少。返回上马时还是让人抓着笼头,当一放开笼头,小花马还是蹦跶了几下,但没有把我尥下来。也就跟着其它马行动起来,顺利返回营房。
从此,随着时间的延长,小花马虽然上马还要人抓,也偶尔尥几下小蹶子,但由于我的警惕,也再没有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调教,小花马总算老实多了,才改换成皮鞍骑乘。骑乘过程中,也确实感到这是一匹好马,大颠平稳,奔驰速度也很快,我还挺有收获感的。可是它的野性还没有彻底改掉,在一次压马(后有专叙)回来的路上,可能是后面的人或马撞到了它的屁股,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尥了一个很高的蹶子,把我摔得翻了一个跟头,落地后我还在地上站着;可见这个蹶子尥得有多狠,劲有多大!因为没有受伤,又是集体行军,我也没当回事,又上马随队前行。
看来这是一次偶然的发作,以后也再没有发生此类事。1967年4月,我调任炊事班长,小花马交由1966年入伍的雷光泰骑乘,他当时已当了副班长。走时我还真舍不得这匹小花马。
再调教山丹“大红马”我调教的第二匹烈马是1966年从山丹军马场接来的一匹马。此马体型高大,毛色赤红,一看就是一匹骏马,所以在分马时就留在了团部,准备作参谋长的坐骑。可是警卫排的战士连嚼口都没有给它戴上过,不久就将这匹马下放到我们四连。大家称这匹马为“大红马”。
我在前面几次讲到过骏马,那么究竟哪一类马才算骏马?我当骑兵整五年,对马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我认为骏马就是马中骄子,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那种特别好的马。骏马有很明显的特征。我以我们四连指导员骑的“15号”(臀部烙印)马为例,对骏马和其它马作一些描述和比较。
“15 号”马体型高大,奔驰如飞,1964年青海海南州举行赛马大会,这匹马取得赛跑第二名的好成绩。此马从外形看两耳尖小、直立,眼似铜铃炯炯有神,显得特别有灵气;鼻孔粗大,呼气时像小喇叭,显得很有气势;脖子接近头部处较细,接近胸胛部位粗壮;胸肌发达,开阔突鼓;腰前粗后细近似狗腰;四肢修长,尤其是后腿曲度较大,奔跑起来弹力极好;四蹄圆而陡立,蹄腕相对较长较细,这一切都显得四肢协调,有线条感,也显得很精干。另外,凡骏马在站立时总是高扬着头,婷婷玉立的样子。骏马在调教好之前,多数为烈马,性急而狂躁。

而劣质马则正好相反,马体粗壮笨拙,没有线条感,头耳相对较大,双目无神;脖子粗细不分明,前后腰一般粗,四肢粗短,像四根直立的柱子,蹄腕粗短,四蹄扁平,缺乏弹力,所以奔跑的速度就慢。这就是骏马和劣马的显著区别。当然,劣马和一般的马居多,骏马很少就不再描述。
前面提到的那匹大红马,和指导员的“十五号”特别相似,下放到四连后,正逢三排放马,八班长也是我的同乡,看见马好就留到自己班里。可是调教了几次,觉得无法驯服,也就放弃了。1967年11月,我们部队奉命到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我也被派去“支左”。回来后任四连一排副排长,因排长调走位置暂缺,由我负责全排工作。
我当副排长骑的是赵连长骑过的那匹老马。这老马是一匹大走马,一天早晨组织压马,其它马都是奔驰前进,这匹老马一直“大走”不掉队,而且感觉轻盈如飞。本来有这样的好马骑应该知足了,但不知何故,我又动起驯服大红马的念头,便和二班长柴俊生商量,因柴班长与我是同乡,人又能干,想让他帮我驯马。
他和我都知道,下一年就轮到一排放马(夏天将我们的马全部放牧到草原上),驯马有的是时间,我们两人一拍即合,便用一匹老马换回了大红马,我有好马骑又为什么要冒险驯烈马?这件事我一直在反思,也一直不得其解。但细思还是有原因的,一是大红马是一匹难得好马,觉得不调教好实在可惜了;二是我好胜心强,想征服这匹烈马;三是精力旺盛,通过驯马找刺激;四是我的骑术是不错,曾驯服过“小花马”,当时也有想逞能因素在里边。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和动机,马换回来了就得调教。当时我坚信,只要驯马的方法得当,再有好帮手,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一定能成功。调教开始,觉得其烈性和小花马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一开始也像对待小花马一样,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但大红马和小花马相比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力量大凶狠,尥蹶子不把人尥下来绝不罢休。

常规调教一个月之后,第一次卸下沙袋,由二班长柴俊生帮着我上了大红马,他还牵着缰绳,可大红马像狗一样蹲在地上不动,我手抓铁环,双膝夹紧马肚,不知它要耍什么花招。猛然间大红马后蹄一蹬,开始尥蹶子,而且是前后腿扬的很高不停地尥,开始我还像黏贴在马背上一样,冷静地数着马尥蹶子的次数,当数到十四五下时开始有些胆怯,担心套镫摔下马来后果难以设想!便双脚脱蹬;脱镫后身体失去原有的平衡,马的最后一个蹶子终于把我尥了下来。因为我有摔马的思想准备,摔马的动作像老连长教的那样,落地瞬间是抱肘的姿势,虽然地面很硬也没受伤。
这下把我气急了,从地上爬了起来,又把麻袋抬上马背骑了上去;大红马又要尥蹶子,可是负荷太重,想尥也尥不起来。我让二班长柴俊生在前面骑马拉上,快跑了近一个小时后,卸下了沙袋我又骑了上去,可能是已累的无力了,也再没尥蹶子。就这样,我们反反复复调教了两个多月,终于见效了,大红马老实多了,渐渐地上马也不要人牵了,行走也不要人牵了,我便换上了皮鞍子骑乘。
所谓第二个不同之处是狡猾,就是大红马不让人骑的时候弹蹄踢镫。人上马时要用右手拉镫在小腹前,脚还没踩到镫上时,它就用左后蹄向前掏弹,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弹到手臂。发现了这一怪毛病后,我有意准备了一条皮带子,掏弹一次,就用皮带子在腿上抽打几下,以示惩罚,此后大红马的这个毛病也改了。
1968年5月,我调到团政治处当工作员,大红马交由二班战士郭x鳌(青海人,和我同年入伍)骑乘,并继续调教。
当年秋收,我作为团工作组成员跟着老连长赵占玉(调司令部待分配)回到老连队。一天下午,放马的回来了,我想看一下自己调教过的大红马,只见郭x鳌骑着光背马已到了马场边。他看见了我,就跳下马迎着我高兴地用青海话说:“副排长,尕马马骑上娆着呢”。意思是骑上舒服的很。
我说:“叫我试一下。”郭老兵随手把嚼口带递给我,我抓住前胛毛要上马,可马就是不停下来,我问郭老兵:“怎回事?”他说:“光背马上就是了。”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手托马背一跃上去了,便加速向前,先是让大走,感觉和老连长骑过的那匹老马一样,骑上速度又快又舒服;返回时,我放马奔驰,只听耳边风声呼呼,霎那间就到了马场门口。我体验到了烈马被驯服成骏马的风姿,觉得当时冒险驯马值得。
至于,上马时为什么马不停下来,当时我并没有多考虑。事后听人说,还有一段故事。事情还要从我们的副连长江德元和他骑的马说起,前面我讲到江副连长是大个子,可他骑的是一匹地产藏马,虽然适合当地气候,耐力好跑得快,也是一匹走马,骑上也很舒服。但马体较小,像我这样个头的人骑上就再合适不过了,可是让江副连长骑上,就显得不太协调;而且此马还有一个刁镫的毛病。何谓刁镫?就是人在踩镫上马瞬间,马体突然左右躲闪,一不小心就会坐空落马。
有一次,副连长带着上士(给养员),到藏族的放牧点联系卖羊的事,事谈妥出了帐篷,在上马间还和藏民(会汉话)说着话;当右腿将要跨过马背时,马屁股蛋突然向左一闪,(可能腿脚碰了马屁股)人体落空掉在马下。江副连长当时就觉得很没面子,藏族兄弟又火上浇油地说了一句:“你这么大个连长,骑个尕马马,不配!”副连长受到这次刺激后,一心想换一匹大马骑,可就是没有合适的。

当发现郭x鳌骑的这匹大红马后,就想调到连部作自己的坐骑。这个风一放出去,这位郭老兄听到后很不满意,就使出一阴招;因为骑兵出去放牧,都骑光背马无需踩镫,手托马背一跃就上去了。这位郭老兄每次上马,都有意叫马在行走,久而久之大红马养成了习惯,人要上马它就是不停。
江副连长不知这一隐情,就把马调到连部,几次想骑就是上不了马,最后只好又把马退回二班。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后,觉得这位郭老兄做事太过分,驯马的目的是为让人骑,一匹烈马好不容易被驯服,而又人为地调教出一个新毛病,这不是又毁了这匹好马?这种行为简直有些缺德。再说,从道义讲这匹好马也应让副连长骑。因为驯服这匹烈马我付出的最多,当听到这匹马的新毛病是人为所致,觉得很痛心!而且还在想,这匹马的新毛病,再有何人、何时才能调教过来?
驯马卧倒和压走马俗语讲:“好马不卧,好牛不站”首先说的是马不卧是天性使然,如果卧倒了就证明有病了。但在实战中,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必须叫马卧倒,这就得进行反复的训练。其方法是,右手拉嚼口带让马脖子右转,同时右臂压马背,左手臂扶马脖子,右膝抵住马前胛窝,让马有依托和安全感。这些动作到位了,多数马就会左膝着地卧倒。因马有不卧的习惯,要让卧倒也不易。所以在驯马时,一般分两步进行,先是不给马备鞍子反复操练,让马养成骑手动作到位就能卧倒的习惯,然后再备上鞍子驯练。

备鞍子训练虽接近实战要求,但在训练中要特别注意一件事,那就是在驯前要把马镫搭在马鞍上,以防马卧倒时镫垫在马身下。如果一旦疏忽,镫垫在马身下,轻者马觉得疼痛,重者还有可能使马的肋骨受伤。不管哪一种,马吃了亏再驯时就有可能不卧了。所以,此类事一旦发生,骑手要及时把镫从马身下拉出,站起后再给予一些安慰,用手按摩马受伤的部位,拉其走动,拍拍脖子,摸摸额头,或给点零食吃,总之尽量让马尽快忘掉这件事。
在这次驯马卧倒中我还吃过一次亏。驯马的第一天,全排的马都能卧倒了,就是我的马不卧,可是偶然一次竟然卧倒了,我趁机从裤兜里掏出马料往马嘴边递,可能是违背了它的习性,不但不吃料,还突然把头一扬要往起站,马头碰到我的太阳穴部位,使我当场晕倒在地,醒后头痛剧烈,一下午再没能参加训练。当然经过几天的反复操练,终于能听指挥了,卧倒、起来自如了。
压走马也是骑兵的术语之一。是对战马的一种特殊功能驯练。说正事之前,我先解释一下“走马”和其它马的有关问题。

骑兵有句行话,叫“小走、大颠,奔子上天”。说的是马在行走中四肢运动的形态及其功能。行话里的这种马,是骑兵最理想的可乘之马,但在现实中只有少数马才三者兼具,多数马只具备一两种功能。概括起来马的运动形态可分三种,一是慢走,各种马都一样;二是快走或叫跑;三是奔驰,俗称挖奔子。奔子上天指的是奔跑特别快。
所谓“走马”是和“颠马”相对而言,都是以马行走的形态命名的。走马的“走”有特定含义,走又分小走和大走两种,小走是小步快走,大走是走的快或很快,有的像奔驰的速度;但走马的出蹄的姿势基本一样,四蹄在交替向前跨越和落地时,形成弧形似画圈,能缓解颠簸。其次是走马蹄腕比较长,且后腿较弯曲,走起来有弹性;再就是行走中,后腰和尾部左右摇摆幅度较大。这三方面因素,人骑上就觉得比较舒适。因为走马行走耗力较大,所以小走马,走着走着就想颠跑,或者是走的快了,就不会用大走的步伐,便颠跑起来。大走马则不然,习惯了走的步伐,轻易不改行走姿势,人骑上就有在水上漂的感觉。
敦煌出土文物“马踏飞燕”塑造的就是一匹大走马的形象。颠马和走马的最大区别是,四肢在交替前行中,四蹄着地几乎是直上直下,反作用在马背上,人骑上就有上下颠簸的感觉。至于大颠马,颠跑的速度快(反之就是小颠马),骑上虽然没有像走马舒适,但只要骑术好,身体能跟上马体颠簸的节奏,也没有多大不舒适的感觉。至于挖奔子,即奔驰,其四肢运动形态各种马都一样,至于奔跑速度,因马而异,区别较大。

所谓压走马,目的是通过骑压使马走的更快。虽不是一项正式训练科目,但骑兵部队的干部战士,只要有条件,都乐意干这件事。当骑兵人人都想骑好马,尤其是走马;就像现代人想买好车坐一样。就士兵来说,骏马那是骑不上的,因为骑哪一匹马,是由领导分配的;但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在一般马中也想骑一匹好些的,尤其是分到一匹有几步小走的新马,还想通过自己的骑压,使其走的更快,如能实现也是个人骑技的体现。
压走马的基本方法是,骑上快走时,脚用力踩镫,臀部压实,上体略后仰,加速时向上提拉嚼口带,不让其颠跑起来(表述不一定准确)。当然,这样的骑压也不是一蹴而就,必须持续一个时期,才能使马走的越来越快,而且逐渐养成快走的习惯。

我们连长马福就是一个压走马的爱好者,但比不上二班班长,二班长1961年入伍,兰州市人,名字忘记了;他在压走马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既有毅力,又能持之以恒的人,也成了一名压走马的高手。他的乘马是1964年接来的新马,生来就会几步小走,和大走马的体型又很相似,为压成大走马,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集体乘马训练外,坚持每天晚饭后把马骑在马路上(那时车少),骑压一两个小时,就是遇到团里放电影他也不去看,坚持骑压。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匹马终于压成了一匹大走马。以后被团里发现了,二班长,1965年年底退伍后,马就调到了团部,成为了政治处副主任张成仁(部队改编后,当过炮兵团政治委员)的坐骑。我调到政治处后骑过一次,果然非同一般,不亚于我骑过老连长的那匹老马大走马。
本刊独家原创 抄袭剽窃必究

刘起来军衔照
作者刘起来 陕西横山县(现为榆林市横山区)人,1946年2月出生,1964年12月入伍,历任骑兵第二师六团四连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团政治处工作员),陆军第二十师炮兵团干部股干事,榴弹炮营一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宣化炮兵学院政治系学员,兰州军区守备一师炮兵团政治处主任,宁夏军区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宁夏盐池县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等职。1986年10月转业,先后任宁夏印刷物资公司副经理、经理,宁夏博誉物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2月退休。
原文编辑:曹益民
本文编辑:徐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