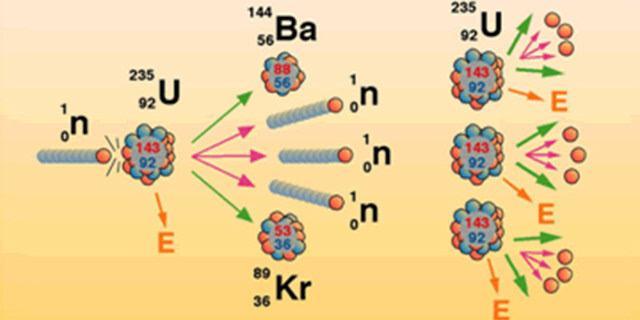作者 | 吴旭
公众号(诗去)
过年了。
80、90一代人越来越忧伤,过年没年味了。
甚至,50、60、70的父辈们,也会在这一共识中,偶尔略小哀叹一下。
是啊!年味去哪儿了?
年味长大了!
回味无穷,甜蜜无尽,儿时那些小幸福,历历在目。
比如,村巷与林间的“火药枪”和炮仗的味道,已经烟消云散;成群的小伙伴欢声笑语中“嘣嘣嘣”的声音,寂静了;水塘里、路洼坑里溅起的发射着泥沙的小水花,再不会起波浪,再不会飞天。
气球里的童年,阉了,喜洋洋气球飞得再高,小孩们的笑脸,比烟花还短暂。电子枪的造型做得越来越威武,用心捕捉,再不见乡间那些四处游窜的稚嫩的神气。
蜘蛛侠像从电视银幕中克隆出来,但得宠也不过三天,便要成为小孩东宫里很难再想起的冷妃。电热炉再温暖,也热不出冬天的“火笼”里,铁盒子中猪油焙黄豆的香味……
这样的年味,源远流长。
往后,取而代之的“年味”,是一年又一年回家的“婚审”,是一轮又一轮尴尬的、甜美的、凋谢的、修成正果的“相亲”。
以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后的人间烟火。
比如,举头三尺有结发妻子,低头一瞬有乳臭未干的小女和小子。
父亲母亲,岳父岳母,把那曾经弥漫着手掌心热的压岁钱,换成了寄托,换成了警训。家庭要美满,妻子要有车子有房子,呱呱坠地的小子小女,未来要能穿好衣,上好学,有个好前途。这样的年味苦涩,道路且长。
以及,那些纯真的鞭炮味儿,也变成了一缕缕春节时候,同学聚会开心热闹的氛围中,夹杂的明争暗斗的硝烟。
比职位高低,比自己盖房还是城里买房,比车子的标志,比江湖的伎俩,甚至泡妞的多寡和优劣。
那些踌躇满志背后,有沉默的紧张和流血;那些西装革履的身旁,衬得几双运动鞋黯然无光。
曾经拿着成绩单在父母堆里争先恐后的“斗鸡鸡”,拉开了真正的架势。
这样的年味,没有对比,也会有伤害。
这些无法规避的成长和抛弃,离别和消失,量变和质变,是一股叮咚叮咚的年味,流向少年的小溪,岁月流逝,小船不可回头。
年味衰老了!
一些外婆、奶奶老了,一些外公、爷爷或许融入另一个世界,开始了新生活。
父亲、母亲胯下那辆“驾式”双枪牌自行车,悲惨在于没机会做古董。那三角架上的木凳子、藤条凳子,也失去了肩负新少主的机会。
晚间的山路,山路里的风声和鸟声,自行车链条吱吱咯咯的伴奏,终被无人捡拾的柴火荒芜。那些山路,早已淹没在林间。那一闭眼,整个世界倒退着的快感,也被初中物理学捻得粉碎。
父亲、母亲一路上串着的各种故事,在脑海中已是模糊不堪。
唯有这一条夜路上的恐惧,和父母双脚与双臂踏出的安全感交错的童年印象,越来越清晰;唯有到外婆家后,用面食油炸的兰花根、红杨梅、糯米片、番薯片、冻米糖,越来越甜。
这样的年味,温暖而慈祥。
那条夜路上,一些父亲挺直的腰杆,越来越弓箭,一些母亲肆无忌惮的唠叨,越来越胆怯。
英姿飒爽的父亲,曾给予童年无数骄傲。母亲脑后挂着的又粗又黑的辫子,也曾入诗篇。
这些构成儿时春节短暂相见的年味,变换了角色。
我们曾在家像禾苗一样成长,父母则外出置办肥料和土壤,只到年终才仓促过年。
如今,父母回到家乡,继续在劳动中安度晚年,我们却又外出了。我们像父母那样一年回一次家时,所痛彻心扉的感知,是父母的白发,和起伏得越来越立体的皮肤。
一些父母花光了一辈子的等待,越来越短暂。一些儿女一年又一年雄心壮志的改变,越来越遥远。
这样的年味,虽无声,却焦急得五味杂陈。
这些无法挽留的慈祥与安康,兑现不及时的给予与成熟,对立着的等待与追求,是一股哗啦哗啦的年味,流向青年的大河,光阴紧凑,时常搁浅。
年味富掉了!
岁月刻骨铭心,那些冰冷的记忆,如今爆发着温暖的气息。
那些打着布丁的袜子和衣服,终止了“流传”的命运。时光,便也终止了等待。
曾经,弟弟的“的确良”,洁净着姐姐的童年;妹妹的“羊绳褂”,污垢着哥哥的淘气。
甚至,大几号的裤脚上,忽隐忽现的父辈们的一辈子,也清晰可见。皮鞋上的油亮,透着村委会一堆“救济物”里,城市的华光。
在这个最好的时代里,我们早已忘掉了过年的等待。每日的每日,都可以花枝招展。每时的每时,都可以款式多样。
一年、二年、三年才一次的期待与快乐,再无法生出肉身和灵魂的触动。塞得满满的衣柜,早已挤出了那个变得陌生、变得无法理解、变得不相信的时代。
与之伴随的被富掉的年味,不仅于此。
比如,家家户户一年才能吃一次肉的过年猪,再难见院子里一刀下去溅满冥纸的血红,和许多时日才能扫去的猪毛。
因此,过年也就没了那份杀猪时,长辈让背过身闭着眼的神秘,和在指尖偷窥的宰杀画面。没了去请叔叔伯伯全家人吃杀猪饭时候的兴奋。
没了大年三十那声声猪叫,年味也淡了许多。
这具体到,或是菜市场买回的猪肉吃的饲料,或是缺了几十号家庭成员围成几桌吃杀猪饭的氛围,又或是一年到头大鱼大肉失去了味觉,过年时再吃猪肉时,已吃不出大蒜辣椒炒新鲜猪肉的甘甜。
被富掉的年味,还有被商品替代了的,母亲漏勺里的油炸圆子等点心,父亲用石磨磨豆腐的幽香和豆腐花的可口。还有那一炉柴火,那一条围裙,木饭桶的木香……
这样的年味,又富足,又遗憾。
这些极难返祖的笨拙与木纳,贫瘠与苍凉,是一股随岁月倒流的苦涩,在愈发富足和新潮的年华里,散发着传统的美、丰盛的缺。
年味退化了!
追求之侧,往往是摒弃。在这个最新的时代里,新和旧也爆发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对立。
这种对立,体现在年味上,就是时下庆贺春节,丢了一地的民俗文化。
比如,向长辈拜年行礼。曾经,北方兴磕头,南方兴作揖、握手等。慢慢地,许多地方开始“一切从简”,从行礼,简化到见面问候,从口头问候简化到钞票。
比如,祭祖。小到家庭,大到姓氏。
家庭祭祖。曾经,吃饭前,无论穷富,吃团圆饭前,必摆上三大碗酒,再摆上三大碗饭,让祖宗先吃,让已故的长者先吃。而今,这样的程序,也逐渐被删减。
姓氏祭祖。那时候,一个姓氏,一个村落,过年时候的祭祖仪式,场面盛大,相当隆重。而今,这样的活动也在逐渐被淹没。
无论是家族祭祖,还是姓氏祭祖,这样的活动除了在幼小的年纪里,丰富了年味的视觉,也增添了族人的交流与和睦。这种仪式感,更言传身教地让后人谨记流传几千年的孝文化。
走花灯,报春闹春等民俗,在“新”的价值观里,褪去了历史的光辉色彩。再难见那些礼节与活动,那些朴实与敦厚。
转而,多了许多集体吸食电子鸦片的低头年味,麻将年味……
这样的年味,也就少了许多厚重感,多了许多媚俗。
这些曾经是一个民族的气魄,一个国家的灵魂,一种社会的活泼,一个姓氏的精髓,在“新”的入侵,和不加筛选的丢弃下,流逝成灰烬。
年味冷漠了!
年味冷却的,除了鞭炮声,除了仪式,还有人心。
这种人心的冷却,由邻里,蔓延到同学朋友,蔓延到家族,蔓延到亲戚,蔓延到整个社会。
如今的亲人团聚,虽也一片热情,一片温馨。但一年一次的相见,遮掩不了社会裂变、生活裂变、感情裂变下,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隔阂与复杂。
比如,功利。比如,嫉妒。比如,交易,比如攀比。血缘和情感的亲疏远近,多多少少参杂着物欲,参杂着心思,参杂着笑脸下的冷漠,参杂着热情下的别样。
这样的年味,多了一些孤独,少了一些纯粹。
这些被生存和江湖带回来的拌生物,像雨一样滋润着血缘和情感,又像秋风一样,在人与人之间染上来历不明的颜色。
年味“升温”了!
种种的种种降温,依旧没有留住雪花。
对于南方来说,一场雪,不仅兆丰年,还兆年味。
雪带来的年味,是雪人,是雪球,是白花花一片银色世界。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乡,已有十几个新年,再没见雪的衬托。
这样的年味,少了许多诗情画意。
环境的变化,不止于雪的归隐。
还有一些地方,被造纸厂污染的,变浑浊的河水,被砍伐一光的少林,越来越少的良田,越来越多的青年绝症者新年离世的恐慌……这些被大肆篡改了的环境,也冲淡了新年的许多喜气与祥和。
每年的每年,故乡都不一样。变得繁华,也变得更危险。年味里这些变化,在这个时刻被集中感知。
这样的年味,少了一些安全感,多了一些伤害。
这些被发展和变迁带来的繁荣与昌盛,危机与破坏,使家乡的年味,多了一些悲悯情怀。
时光在流逝,民智在开化,精神需求在增长,信仰在缺失,年味越来越浓,又越来越寡淡。
哦!年味,都去了得与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