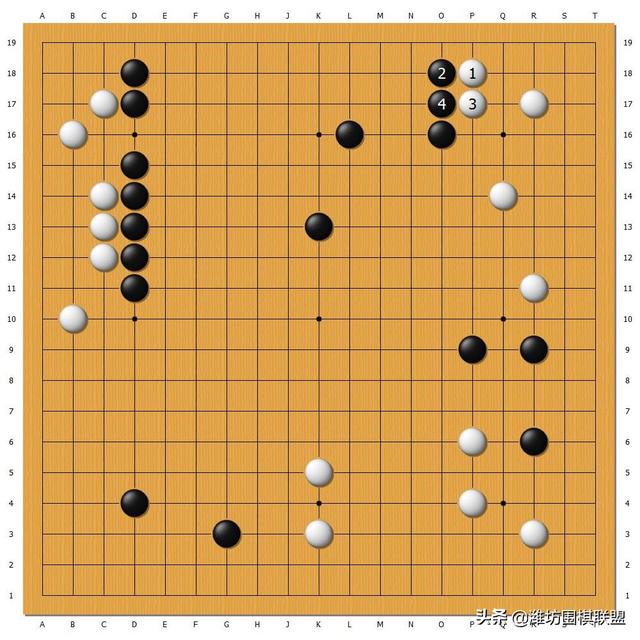在乡下老家,流传着“养鸡为兑盐,养猪为过年”的俗语,简简单单的10个字,足以概括当时农村生活的艰辛,养鸡不为自食,只为补贴日常农用,至于猪肉,平时难得吃上几回,过年了,杀一头自家喂的大肥猪,一方面备以过年,二来,可以卖一些猪肉,春耕以及年后孩子们的开学都需要钱。
进腊月了,“杀猪”一事提上日程,父亲早早就开始准备——请杀猪匠。那时的农村,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个杀猪匠,他们并非职业杀猪匠,其实也是普通农民,日常以田地为主,逢年过节有人家要杀猪了,他们才操起手艺,游走村庄,挑战一头头大肥猪。
印象中,那时的杀猪匠都膀阔腰圆、孔武有力,或许,只有这种身材的人,才能镇住猪吧。村里的华子叔就是如此。父亲与华子叔关系极好,上门说明情况后,华子叔二话不说,一把答应下来,并且还为父亲插了个队,提前杀猪。

杀猪日子定下来了,父亲开心地走东家串西家,告知村人我家要杀猪,需要买肉过年的,到时去买。忙完这些,父亲又找到隔壁左右的几个男主人,请他们杀猪时去帮忙,几百斤的大肥猪,光靠华子叔和父亲,断然成不了事。
杀猪时刻终于到来。一大清早,母亲就起床烧起土灶,前后两个大锅都盛满了水。华子叔也早早过来,一担“装备”在他肩上轻松得很。扁担一头是一个大大的木盆,另一头挂着一个老旧的帆布包,以及一张宽阔厚实的长条木凳,包里装满刀具及相应工具。
几个人走进猪圈,那头大肥猪似乎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断往墙角退。华子叔一个箭步上前,一手揪住耳朵,另一只手上的铁钩立马伸进猪嘴,往回一拉,牢牢勾住。此时,其他的几个人拉的拉尾巴,按的按脚,大肥猪在众人勾拽推拉下,拼命嚎叫,往宽阔木凳处挪动。

平日笨重的大肥猪,此刻不断挣扎,不断嚎叫,年幼的自己在一旁既兴奋又有些害怕地看着,紧张、激动,生怕大肥猪从众人手里挣脱,冲了过来。猪被按在了长凳上,华子叔拿出一柄亮闪闪的尖刀,对准猪的颈部就刺了进去,顿时,一股鲜血直喷,进入下面的盆里。
嚎叫声渐弱,终于不再动弹。几个按住大肥猪的人,这才松了手。父亲一边拿出烟,分发给各位帮忙的人,一边忙着把母亲早就烧好的开水一桶桶地倒入华子叔的大木盆。此时,华子叔从他的帆布包里取出一个粗壮的打气筒,又拿了尖刀在猪腿上开了个小口,而后,一个人把打气筒的出气管子放入小口中,并用力按住,另一个人,则开始不断打气。
不一会儿,那头大肥猪就变得气鼓鼓的,浑身被胀了起来,当时的我觉得很新奇,怎么还要跟猪“吹气球”呢?鼓胀鼓胀的大肥猪被抬到装满开水的大木盆里,华子叔取出一个铁皮刮板,开始在猪身上不断刮行,白白的猪毛,顿时落入盆中。

木梯已架起,几人合力将猪抬到木梯边,华子叔又拿出钩子,一头勾住猪嘴,一头挂在木梯上,那头猪就被吊了起来。随后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华子叔拿出刀,开膛破肚,猪的身体结构好像在华子叔面前早已谙熟无比,无需多看,刀随眼到,片刻即成。
内脏被取了出来,摊放在家里的大簸箕上。此时,母亲走了过来,将还冒着热气的猪肝拿到厨房,切片打汤。在老家的习俗里,请人杀猪,是一定要做一碗猪肝汤的,以酬谢前来帮忙的人。几碗鲜嫩的猪肝汤瞬间即成,碗中还卧了两个荷包蛋。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家伙,也会分到一小碗,鲜嫩爽滑,汤汁浓郁,我们恨不得把碗舔个干干净净。
猪肝汤喝罢,众人又开始忙活。村人早已围拢过来,这家买个前腿,那家买点肉,华子叔手起刀落,砍出一块块村合乎心意的肉。要不了多长时间,计划中的猪肉就已卖完。那时乡情淳朴,有钱没钱的,都要捧个场,同村的乡里乡亲,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尽显农人友善。

一切收拾妥当,接下来,就是重头戏。杀猪了,当然有一顿大餐,猪肉下锅,各种做法——清炒、红烧、煨汤,一碗碗肉菜摆上饭桌,华子叔与其他帮忙的伯们一起落坐,此时就热闹了,酒兴大起,划拳喝酒,一个个喝得脸红脖子粗,哪怕走路歪歪斜斜,依旧酒兴不减。父亲更是开心,春耕有了指望,我们的学费也不用愁了。
“杀猪”至此结束,华子叔收拾着他的装备,准备回家。父亲早已递上工钱和香烟,也不忘把清理好的猪鬃和小肠递到华子叔手上。老家的规矩如此,不知始于何年,记忆中,不管是哪家杀猪,猪鬃和小肠必须留给杀猪人。
每逢年关,总会想起乡下老家关于“杀猪”的往事。或许因为贫穷,那时的农人把“杀猪”当成一件大事,热闹又喜庆,为“过年”打下丰盛的物质基础,也浓重地渲染着年味。如今,自家杀猪的越来越少,猪肉,更是日常餐桌上的标配,乡村杀猪匠,好像也越来越少了。#冬日生活打卡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