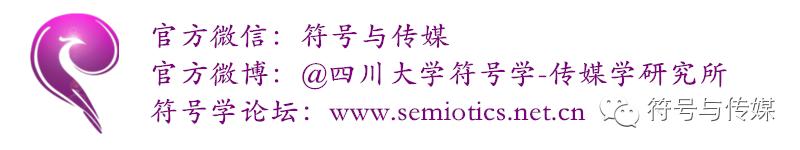
摘
要
镜像在不同文化中均具有极其特殊重要意义。在符号学研究中,学者对待镜像观点迥异,艾柯甚至宣称镜像不能被作为符号来看待。在一系列镜像符号属性论辩的基础上,本文以“镜像是自指性元符号”为命题,从“生物演进”“个体发展”“社会身份”多层面来阐述镜像符号所具有的形式典范性:对于生物或人类个体的自我建构,镜像符号具有一种元符号能力的评价功能;同时它也是个体在社会文化中自我定位的标记方式。镜像的特征使得它成为诸种像似符号的“基型”。作为意义生发的“奇点”,其不同方式的衍义可生成像似符号的无限可能形式。对镜像符号的理解,应超越结构层的属性探讨,进一步与文化自我意识等一般性规律结合考察,旨在从符号学角度对镜像这个特殊文化符号提出更为明晰的形式规律界说。
关
键词
镜像符号 艾柯 自我意识 认知科学
引
言
镜像所具有的特殊神秘气息与魔力几乎是超文化的,中西文学与神话不约而同赋之以神奇的力量。不只人文学者和艺术家为之着迷,社会学家也认为它是主体建构的核心策略之一;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无不牵涉镜像的问题。很少有哪种事物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文化意涵,同时又造成如此之多的困惑。这些跨学科的共同探讨主题是罕见的,其原因可能是镜像问题折射的形式问题具有普遍性:个体镜像是个体意识的反映,社会镜像是集体或社群意识的体现,而物理学家甚至将反物质称为“世界的终极镜像”。由此,作为意义之学的符号学或能尝试探讨其表意形式规律。具体讨论方式则可以是抽去个别镜像的内容而通过它的一般形式去理解镜像。这就有必要悬置某具体镜像的内容,而将其形式特征作为讨论对象。

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要弄清楚,当我们说“镜像”时,我们在说什么?其中的一般性规律对我们理解意识具有何种价值最基础的,至少是界定镜像是否身处符号的讨论范畴之内。如上所述,镜像的诸种复杂象征意涵是一个显见事实,但符号学家却一度考虑将镜像从符号家庭中除名,重要的文献之一是艾柯为其英文版《符号学与语言哲学》撰写的《镜像》一章。在此章中,艾柯以镜像为对象,讨论了符号的基本条件,并以这些条件为评价尺度否定了镜像是一种符号。他指出,将镜像从符号群类中排除出去,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定义符号,或者至少定义符号不是什么。此论引起了符号学者们的论争,李幼蒸、赵毅衡两位先生的论辩最具代表性。李幼蒸认为艾柯所列条件不能排除镜像的符号属性并侧重说明镜像与原物意指关系成立。赵毅衡的逐条辨析更为细致,并针对每一条提供了丰富的论辩例证。他指出,既然存在解释空间,则镜像依然是符号,且任何镜像都在符号的门槛之内。两位学者的论辩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不过,对像似程度过高问题的讨论似乎尚有余地。艾柯否定镜像为符号的理由之一是“不能解释以及无法撒谎”,尤其强调“镜像只是重复”,因为镜像是拥有“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的图像……因此,不能用像似原理来解释镜像。艾柯还提出,镜像只有降低像似程度(他举了烟熏的镜子一例)才能成为像似符号。
可以说,艾柯拒斥镜像进人符号世界的理由是他设定了一种“零度镜像”,这种镜像绝对真实可靠且不形成任何误解。不仅如此,他还预设了对镜像的具有零度解释的解释者。这导致了镜像作为一个文化社会中的事物被抽离而进人了一种非符号化的工作假定之中。实际上,从艾柯否定镜像的理由以及让镜像进人符号门槛的策略来看,“像似程度”是一个关键点。基于此,笔者曾撰文分述了“绝似”“重合”“副本间关系”甚至“原物自身”如何生成符号意指关系,进而指出艾柯对于镜像的论辩之失在于:他高估了镜像与原物的“重合程度”,又低估了镜像的说谎能力—镜像并不是原物的“重合品”,它只再现原物冰冷而无法触摸的视觉部分而非原物的“全部品质”。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此,本文就初具在符号学范畴内讨论镜像问题的基础。并且,由于前述诸文着重镜像是否为符号的论辩,对镜像这一深具魅力的符号形式的分析则需要更多后续展开。由是,本文不仅是镜像符号身份的论证,更希望以此为起点深人镜像作为符号的一般性规律考察。在前述基础上,可尝试对镜像这种特殊符号作一个界定:镜像,是一种释义者与发出者具有同一身份的自指性元符号。简言之,镜像是“符号自我”的基本形式。其特殊性包括绝似性(三位一体的)、在场性、自指性、元认知性和具身性。上述特性的极端形式全部满足,即同一的绝似、零度符号距离的在场、封闭的自指、唯一化的元认知,则可能构成艾柯所说的“零度镜像”。零度镜像只是一种工作假定,在实际符号世界中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异都会造成符号释义的展开和符号形式的无限衍义,其衍义结果可以构成其他任意形态的像似符号。
一
符号距离与像似变异
通常认为,绝似符号在皮尔斯符号分类中是像似程度最高的像似符号,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在符号表意效果上因符号再现体与对象的接近而导致实有其事的误会。赵毅衡指出,绝似符号只是错觉,并没有到绝对同一(sameness)的地步,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符号过程。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符号与对象完全看不出区别,则称为“重复”(double),重复是否是符号关系是有条件的。此处,是否重复取决于观察者是否“看出”。这个判断用于“镜像”的理解中,可以解释为在未被识别的情况下,镜像也可能是重复。但此时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预设观察者的“无知”—当且仅当此种情况下,艾柯预设的那种绝对真实的“零度镜像”才成立。不过,此时它不仅不是符号,也不能说它是“镜像”,因为并没有一个观察者来界定所见之“象”与原物的关系。艾柯的误会即是用假设的上帝视角来说明镜像的性质,却要求解释者对镜像这个“元符号”保持绝对的无知,以至于可以把镜像中“象”的呈现视为真实本身。艾柯认为烟熏镜子的镜像能进人符号的门槛,这种策略缺乏一个抽象逻辑,它太形而下,也太机械了。
任何符号形态在被观察之前,都类同于一只“薛定谔的猫”,它类似于不确定的量子态。我们引人了“镜像”概念,也即引入了“观察者”,就好比处于量子态的对象在瞬间坍缩为可见的符号—像似符号,且是其中像似程度较高的绝似符号。如果进一步演绎这种被设定的具体条件,就进人了更为具体的演绎过程。艾柯所提的烟熏在降低像似程度方面其实并没有任何效果,它只是增加了符号传播过程中的“噪音”。艾柯还提到,多重折光的剧场拉开了传输的距离,哈哈镜导致了变形等情况。这些方式都从某个侧面使得镜像原物与再现体之间的异质更为明显。其中,他提到“照片是凝冻的镜像”,这就是将镜像的时间同步性抽去了。这就涉及到他反对镜像作为符号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理由:符号再现体、对象与接受者的在场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场性也是镜像与一般符号的不同之处。通常认为,绝似符号与对象并非同时在场,因此它们明显是代替对象的符号。同时在场是否构成符号的必要条件,李、赵两位先生都已经作了充分论辩,此处不赘述。但“在场性”乃是镜像不同于一般符号的明显特质。作为从假定的零度镜像出离的符号表意过程,对象与再现体同时在场,仅仅意味着三者有相对较近的“符号距离”。这种较近的距离是镜像发生演绎的初始“符号距离”。通常认为符号距离有三种: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表意距离。艾柯用在场性来否定的只是时间、空间距离相对较短,但未能否定任何一种距离之存在。当三种距离都为零的时候,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零度符号态或称为零度镜像。此时,符号处于混纯,而意义也就无从言说。一旦一种距离开始产生,意义世界的奇点就出现了。镜像的方式是符号表意距离出现的最简形式,相对于一般符号表意过程,镜像需要的实际要素最少,接受者-解释者-对象三位一体,且因为同时在场而具有极短的符号距离。在这三个距离中唯有“表意距离”才是符号存在之根本。时空距离对于符号表意来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发生演绎的初始点。如果一种符号表意没有时空距离,则意昧着它没有传播性,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时空的初始距离构成了一个符号衍义的“原点”,之后,随着符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递,世界成为符号构筑的文化社会,符号不断衍义、累积,并以几何级的方式向外膨胀。这个膨胀过程即符号诸形式在文化社会中的无限衍义。严格意义的“再现体-对象-接受者三位一体”和“共同在场”的距离被拉大了。符号距离在技术和文化的多样性中更具跨越性,并且更加丰富。艾柯所称的变形了的“镜像”(直播、电影等)实际上是在符号距离上不断跨越的结果。并且,在这种跨越过程中,局促于原初样态的符号表意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的路径在理论上是可追溯的。空间上,对象与符号同时在场的距离被逐渐拉远,最初产生折光剧场、实时转播,最后这种距离可能是跨国甚至越洋。这种空间距离本身也意味着时间距离的出现,不仅是光线传播本身具有时滞,而且有实况转播为了提供意外画面出现时的应急切换还有人为时滞。最终,时间或空间距离拉大到可以跨越整个人类文明时空的两端:先秦竹简或石刻上的符号跨越数千年向我们展现当时的文明,而现代数字媒体跨越整个地球传递大洋彼岸的实时图像。在这种时空距离的传递过程中,镜像符号的像似程度也会发生前文所述的各种变异。
二
镜像作为自指的元认知符号
(一)、镜像自指及其具身性
自指性是镜像最直观的特性,也是它关涉“自我”的原因。只有当观察者自身置于镜子之前并以自身为观测对象时,镜像符号才具有了那种不同于一般符号的特殊形式—原物与对象常常同时在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艾柯才认为它应被逐出符号家族。因此,此处对典型镜像的界定必须包括“自指”的特性,否则就失去了划定镜像边界的重要依据。一切借助某种光学媒介手段形成的“视觉图像”均是镜像,意味着一切都是镜像,而这无异于让镜像失去了基本特征。一旦通过镜像来观察他物,镜子就变异为与一般媒介物作用毫无区别的类折光剧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镜像的这种自指特性来说,它的基本表意形式即“图形对象”主体关于“自我”的认知—在其意义上可看作哲学上古老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人类在自我认知历史上,曾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人类这一物种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卡西尔在《人论》开篇即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但对现有结果的深究表明,人与动物的差异往往不能通过某种单一界限加以界定。换言之,很难从单点出发论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绝对界限。例如,亚马逊丛林中的卷尾猴可以使用简单工具,黑猩猩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蚂蚁或者蜜蜂的社会化分工极其有效,甚至道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并不能完全将动物与人分割开来……随着生物符号学的进一步推进,卡西尔笼统地通过“符号动物”来界定人的独特性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考证。人类自我确证日渐被理解为多维度的复杂性问题。正如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曾经焦虑的那样:“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复杂性本身当前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否认的理解方式。就“人”的独特性而言,要做的只是在人类不断自我建构中实现“人”的总体性价值,不断地用新证据实现人的自我建构,而非给出一个固化的终极答案。卡西尔即便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也保留了对动物的开放性。他指出:“对这个问题(类人猿的符号化过程)的未来发展作任何语言都是为时过早的。这个领域必须为今后的研究始终敞开大门。”
本文所涉的“镜像”亦是如此。科学实验表明,除了人类,经驯养的黑猩猩、大象、海豚以及某些鸟类(如喜鹤)有照镜子的能力。法国儿童心理学家亨利瓦隆的“镜子测验”表明,人类在肢体协调性方面即便弱于其他动物,但在领会自身镜像关系方面却更有优势。这似乎表明,镜像识别是智力中比较特别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不完全与记忆等其他智能等同,它有关自我,是人类信息认知结构中占据信息主导地位的视觉符号形式。符号哲学家诺伯特威利指出:“自我是一个符号(或者记号)……自我由符号元素组成。自我不再是指一种机械的或者物理学意义的性质,而更是一种文化的性质。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一层是指,所有的自我—不管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拥有相同的本体意义上的品质或者说相同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镜像的认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因为只有“我”存在,人类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才可能具有更进一步的自我意识显现。“我”是从动物到人的漫长演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镜像符号能力,对于“自我”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明晰的节点。
(本期编辑:伏昱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