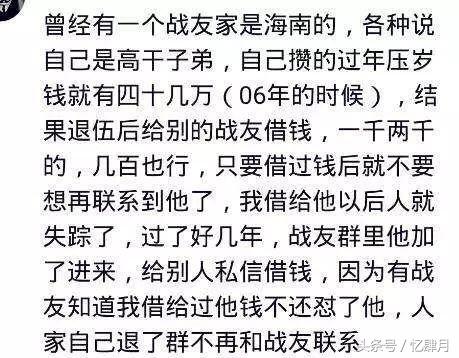一、反讽“副解归正”
解释漩涡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符号意义解释方式,但是至今没有被重视,主要原因是它与反讽—悖论以及一般的“双读”,不容易区分。本文在讨论解释漩涡前,先要仔细区分这些容易混淆却极不相同的表现—解读方式。如果我们弄清了它们的根本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全球性文化正是从现代性的反讽主导,逐渐移向后现代的解释漩涡主导,混淆这二者,会让我们看不清当代文化表意方式变化的大势。二者的区分,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格的分 类方式问题。
哲学、修辞学、符号学、叙述学、文化学,都讨论反讽问题,反讽的确在人类的意义生活中非常重要,而且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到来,在许多领域变得更加重要。而解释漩涡的重要性绝不会低于反讽,只是其意义机制经常被忽视,或与反讽混淆。二者的区别实际上很容易讲清楚。符号表意文本,尤其是艺术诸体裁,或是沾有“艺术性”的体裁,如广告、招牌、取名等,经常会引出双读——两种不同的解释。反讽与解释漩涡,都是利用双读的文本形式。这是二者容易混淆的原因。
反讽引出的双解,是一反一正,一字面义一隐藏义。它是一种超越修辞格的意义方式:各种修辞格都是比喻的变体(转喻、提喻、曲喻等),象征是比喻意义的加强延伸。各种比喻修辞格,目的都在于在符号再现与意义之间寻找异中之同,比喻各修辞格是把再现与意义从远拉近,然后可以比附。象征也只是把这个功能变得更抽象。而反讽迥异其趣,是取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意义,放在一个符号表意方式中,目的是寻找符号再现与意义的冲突,从而让解释者读出一个特别的意思来;比喻各修辞格是手段各异地互相接近,反讽却顾左右而言他,欲迎先拒,欲擒故纵,表达出来的与真正的意义正好相反。比喻修辞格疏导传达,使传达易懂;反讽存心搅乱这个程式,让意义传达变得困难,反讽有意扩大表达方式与期待的解释方式之间的距离,因此是一种张力十足的表达方式。
悖论是反讽的一种常见方式,有人认为悖论与反讽并立,笔者认为可将悖论视为反讽的一种亚类。反讽(irony)与悖论(paradox)的文本构成方式不同,反讽是“口是心非”,再现与意义的冲突发生在两个不同层次。表面义有意说非,期盼读者解释义为是,而且只取后者为正解,例如《红楼梦》说贾宝玉“天生有下流痴病”;悖论是“似是而非”,在再现文本中列出两个冲突的意思,期盼在解释中合二为一,取其一者为正解。悖论与反讽的文本机制与解释机制是类似的,只是悖论的冲突显现在文本中,例如“沉默比真理响亮”。
反讽与悖论二者都是自相矛盾的意义方式,都是旁敲侧击,在许多思想家的分析中,实际上二者混用。克尔凯郭尔的名著《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是反讽理论的权威之作,此书开场列出15条反讽论点,第一条是“苏格拉底与基督的像似之处恰恰在于其不像似之处”。这是一个悖论,因为矛盾双义都现于文本。克尔凯郭尔对此还有个注文,解释为什么两者既像又不像:“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门徒们知道:‘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而苏格拉底的真理是隐蔽的”。基督之言是直截了当的声言,苏格拉底用欲擒故纵的反讽,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克尔凯郭尔全书最后归结于一条拉丁名言:“因其荒诞而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反讽研究史的开山之作,却用悖论开场,用悖论结束,因为二者表意的本质是相通的。
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一书中说:艺术语言必定是悖论语言,他认为悖论分两类:“惊奇”与“反讽”,即是说,反讽是悖论的一种。但是此人另一篇著名论文,却题为《反讽——一种结构原则》,此文坚持说:反讽是艺术的普遍本质,诗歌,以及一切文学艺术,其符号表意,必定言意不一,言非所指。对反讽作如此宽的理解,最基本的反讽就是“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扭曲”。这样一来,当然悖论就是反讽的一种。
到底何者包括何者?从修辞学上说,两者表意方式不同,应当分开,反讽的期盼解释在文本之外,而悖论的期盼解释在文本之内。布鲁克斯把反讽与悖论都用于最宽泛的定义,以此为艺术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根本特点,即避开意义直指。在这个目的上,二者不严格区分,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悖论文本上的双义矛盾,还是反讽的文本义与解释义矛盾,都是在冲突中才能取得意义合一。
反讽与悖论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解释者的“矫正解释”,在两个意义表述中二者取一,而矫正靠的往往是文本的伴随文本语境。许多符号文本是多媒介的,文本边缘不清,不像语言文本前后边界明确。这就是为什么反讽在诗歌中使用得更多。例如岑参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字面描写的是梨花,实指义“大雪”落在标题“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个副文本中。如果文本包括标题,就成为显示双义的悖论;如果文本不包括标题,只看诗句,那就是反讽,实指义藏在语句意义后。
幸运的是,在这个例子上我们还能区分反讽与悖论。一旦分析多媒介文本,各种媒介可能互相冲突。只算单媒介,往往为反讽;联合多媒介,即成悖论。在多媒介文本分析,恐怕再难区分反讽和悖论。例如,一个人说“今天的讲话真精彩!”但是他在玩手机,脸上表情诡异,时间已经不早,我们就知道此话是反讽;如果我们把手机、微笑和时间看作一个联合文本,他的话就是悖论。
悖论、反讽,都是曲折表达,解释者都可能没有理解正确,因此不能用于科学/实用场合,因为要求表意准确。悖论与反讽最常见于哲学和诗歌,到现代,成为最基本的艺术表意方式。
二、 双读与解释漩涡的“亦反亦正”
反讽与悖论都是双读现象,只不过在解释中必须得出明确的一义,也就是成功的解释可以消灭双读,得出一个意义解释,这样就是“表面双读,意义归一”。应当说,反讽与悖论并不是真正的双读。
真正的双读,是文本有两解,一个不能取消另一个,两个同等有效。双读有两个类型,首先是一读一解,另一读又另一解,两种读法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解释中。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与非有彼此之分:此解为是的,彼解为非,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大量出现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双读图形中。表面上看图形可以有相反的解释,但是这两个相反的解释,在一次解释中会达到一个暂时稳定的解读。例如最常见的奈克尔立方体(Necker Cube)的解读,床单式的深浅间隔平面的立方图像,很容易被解释为立体对象。解释者看到突出的方块,凹入的方块就成了背景;下一次看到凹入的立方体,突出的就成为背景。采用一种解释,条件是排除另一种解释,哪怕暂时搁置另一种解释。
双读不是反讽,因为反讽只有一者是正解,另一者是配成的副解,不可能成为正解。上引岑参名句,写的就是大雪,写梨花是副解。而双读不然,例如老板说:“放心,我不容易生气”,这可能是安慰,这也可能是威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此话的文本义与意图义不合,是反讽;但是它也有可能引向字面义,也就是安慰。这时两个解释都不能否定另一个,无一正一副之分。要得出有效的解释,就必须根据场合、表情、此人一贯的行事风格,来做评断。无论如何,“安慰”与“威胁”落在两个不同的解释中,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解释者最终只能采用其中一义,看来两解中也只有一义具有真值。
如果在对同一文本的同一次解读中,出现了两个解释,而且一者无法取消另一者,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时就出现了双义同时被采用而形成的“解释漩涡”。我们拿很多艺术学家讨论过的著名的“鸭—兔”图为例,贡布里希认为:“我们在看到鸭子时,也还会‘记得’那个兔子,可是我们对自己观察得越仔细,就越发现我们不能同时感受两种更替的读解。”他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说“鸭—兔”图与其他格式塔心理学测试没有什么不同,是二解双读,至今不少论者同意此说,例如韩国艺术学家朴异汶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同一种事物不可能同时成为兔子和鸭子,而这幅图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有可能以两种形象来加以解释。”但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却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鸭兔实际上并存,并不是看到鸭就忘了兔,看到兔就忘了鸭,两种冲突的解释不可能也不必互相取消,这张图就从普通的双读变成解释漩涡的妙例。琳达·哈琴在解释反讽语义的包容性特征时,也用了这幅图来说明。她说:“如果论到反讽意义的兔子和鸭子,我们的心灵却几乎可以同时体验两种解读。”他们的意见即是解释漩涡,可见(两次解释的)双读互易,与(同一次解释的)解释漩涡,分界不一定分明,要看解释者的处理方式。但是至少这个著名的例子说明了二者的解释方式截然不同。
荷兰木刻家艾歇有很多画作都在致力于推翻格式塔的二解双读,而致力于创造同一次解释中有双解并存,也就是说创造解释漩涡。艾歇有大量背景与前景互换的画,平面翻成的两种立体面,不但可能有双解,而且要求同一解释中必须双解并存,例如标题就注明《鱼与雁》《天使与魔鬼》,不同时读出双解,就没有读懂这样的解释漩涡作品。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解释共存于一解,但并不如反讽一者取消另一者。这是艾歇作品的魅力所在:天使与魔鬼并存,解释者也必须同时认知两者。
三、解释漩涡的普遍性
解释漩涡其实非常普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常见的解释漩涡,是戏剧电影等表演层次与被表演层次之落差:在表演层次,历史人物长了熟悉的明星脸,明显为假,怎么可能让我们替古人担忧伤心?实际上,观看演出时,解释漩涡已经成为我们观剧的文化程式,观众既看到演出,又看到被演出,二者不会互相取消。观众对明星脸的认读,应会破坏影视戏剧的“真实感”,让银幕上的历史不可信。此种解释漩涡,却是观剧常规。
戏曲演出中经常会出现矛盾的解释:女主人公悲伤拭泪, 而就在悲伤情最深处, 呜咽转入哭腔, 悠长而响亮, 观众一片掌声喝彩。他们激动有两个原因:被“孝女贤妻”真情打动,同时,也被媒介本身的形式美打动,这就形成了解释漩涡。表现与被表现两种解释之间的漩涡,正是影视戏剧的魅力所在。如此的漩涡可以出现于所有的艺术:很难把符号文本的形式与内容隔为两个层次分别处理。
例如范冰冰在电视剧中扮演武则天,演者是范冰冰,被演的是武则天,对大多数观众来说,两个解释并存形成解释漩涡。表演的文化程式,使观众可以而且应当接受这个同时双解。假定范冰冰穿上武则天的龙袍出来为新片“站台”,就是反讽:站台宣传不是艺术演出,是日常生活。日常/科学的表意不能允许解释漩涡。
这不是说科学中无解释漩涡,“薛定谔之猫”就是一个解释包含互相不能取消(猫既活又死)的双义;平行宇宙论,也是说发生的双向宇宙,一者不能取消另一者。本文说的是描写这种现象的科学语言本身,不能不分彼此是非,引发解释漩涡。解释漩涡让交流产生阻隔,但是生活中也会遇到解释漩涡,尤其在日常生活被“艺术化”的场合,更是如此。
此种双读并存,也适合于所谓“斯特鲁普效应”(Stroop Effect)。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斯特鲁普(John Riddly Stroop)在1935年发现的符号解读冲突方式:写一排颜色字“红黄蓝白黑”,但是“红”字用黄色,“黄”字用蓝色,如此等等,此时语义层文本(即字义“红黄蓝白黑”),与字的形式层文本(颜色“黄蓝红黑白”)会发生冲突,解释者会不知道如何解读才对,两种不同的读颜色的方式会发生冲突。应当说两种读法都是有根据的,一者无法取消另一者。解释者面对这一种写法里的两个文本,加工方式不同,想只解释其中一个文本,而完全拒绝另一个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辨认字义在先,还是辨认实际色调在先,实际上要看解释者根据情境做出的选择。
斯特鲁普效应随处可见,应用面极广,经常见于广告招牌等图像设计,例如招牌“竹苑”,字是竹子一节节拼搭而成;冰淇淋店“冰爽”会画得冰冻霜结;“焦点”电影公司的幕页或故意让“点”字虚焦;谋杀恐怖电影,标题似乎是手沾鲜血涂成;追车电影,则总是字体倾斜,似在疾驰。由于我们对文字熟悉,我们经常把它称为“美术字”,但如果我们不熟悉这文字,那么我们的解释中,图像意义会优先。我们一般采取双解之一,而把另一者暂时悬搁。这是解释漩涡的题中应有之义:“鸭—兔”画,对于熟悉兔子的人,会兔子占优;范冰冰演武则天,不熟悉范冰冰的人,会武则天占优。解释漩涡只是针对设计者的“意图定点”,即“解释社群”中的多数人的认知水平,才充分有效。
应当说清楚的是:如果对一件事,有先后两个不同的解释,且分别采用不同的解释规则,不会形成解释漩涡。在面对同一现象或文本时,两套不同的解释标准,在同一个人做同一个解释时起作用,才会形成解释漩涡。著名的电车难题,前面有两条轨道:一条上坐着一名幼儿,开上此道会压死孩子;另一条轨道通向悬崖,会危及全车人的安全。对于功利主义而言,因为追求“多数人的利益”原则,故而应该通过牺牲少数拯救多数,但是对于道德主义而言,杀死毫无防御能力的幼儿,是道德大忌。在解释的关键时刻,如果电车司机使用两种无语言,他就悲惨地落入了一个解释漩涡,他没有重做解释的机会。
四、社会文化中的解释漩涡
实际上,解释漩涡虽然是笔者的命名,却不是笔者的发明,古人早已多次论及。孔子《论语·颜渊》有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既爱又恨造成的“惑”,就是解释漩涡。父母很爱自己的孩子,但自己的孩子闯祸犯下不争气的错时,恨不得从来没生过他。爱恨交织,同时存在,无法互相取消。
孔子说过,佛陀也说过。《金刚经·大乘正宗分第三》中,佛告诉须菩提如何发普救众生:“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佛陀指出,凡是趋入大乘道的菩萨,应当度量无边的众生,应当让所有生物远离轮回的痛苦,获得究竟涅槃度化,求证无上菩提。但是“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讲的世俗菩提心。但在实相中,无有众生可度:被度化的众生、能度化的菩萨,如虚空般皆不存在。这是对同一事不得不有的双重理解。
西方也有此说。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积极的时代,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消极的时代?或许乐观者倾向同意前说,悲观者乐意同意后说,但是狄更斯提议我们兼顾双说。解释漩涡或许是对时代最准确的解释。
至于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解释漩涡,那就更多了,解释漩涡实际上是艺术作品最令人争议不绝又回味不绝的情节构筑,是让艺术文本在道德冲突上避免简单化的最好办法。金庸《神雕侠侣》第十一回“风尘困顿”,用杨过的视角,写北丐洪七公和西毒欧阳锋在华山第三次相遇比武:“杨过见地势险恶,生怕欧阳锋掉下山谷,但有时见洪七公遇窘,不知不觉竟也盼他转危为安”。欧阳锋是他的义父,自然不希望看到他比武失败;洪七公慷慨豪迈,当世大侠风度令他心折。两人也已经历了患难生死,自也不希望洪七公出事。但比武必有胜负,必有伤害。这次比武,在同一主体杨过的同一次解释中,无法取舍,形成了解释漩涡。
甚至现在越来越重要的科幻小说,依然不得不依靠解释漩涡。小说《三体》中,作为第二代执剑人的程心,在三体人进攻地球的最后一刻,放弃了发射地球人建立的用于制衡三体人的威慑系统引力波宇宙广播,这原是用以向宇宙发射地球坐标。公布地球坐标,会引发来自宇宙其他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三体文明也会同样遭殃。他的放弃,导致了三体文明掌控地球,人类被驱逐到澳大利亚。这一行为让人类惨败,可以说是对地球最大的恶;同时又是对两个文明最大的善,让两个文明得以在宇宙中安全存在。大恶和大善成为难以相互取消的解释旋涡。主人公痛苦不已,因为他做了一件无法逃脱解释漩涡的事。
进一步说,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更是解释漩涡的重要发生地。艺术的特点就是非单一意义,导致多样化解释是必然的,甚至同一个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原则,采取几种解释。胡适的《尝试集》以平白、朴素的口语,代替了“风花雪月、娥眉朱颜”等“诗之文字”,形成了对古典诗歌“诗美”规范的反动,让早期新诗以清新的活力和历史包容力开场,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同时我们也感到《尝试集》是失败之作,原因正在于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诗美”,失去了“诗味”。这两种看法无法互相取消,形成解释漩涡。
许多熟读古典文学者,对“元白诗派”的评价也是如此。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中唐诗派,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诗歌应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社会价值意义上非常值得称道。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诗歌语言浅显易懂,老妪能解,失去了含蓄蕴藉之美。对元白诗派的评价由于解释的双重标准,即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可以得出相反的评价,两者不能相互抵销。
再例如纽约联邦广场上的铁制雕塑《倾斜的弧》,是一座纪念碑式的钢铁弧墙。此雕塑将广场一分为二,附近大楼的职员必须绕过它才能进入办公室。作品马上引发争议,一部分人要求移除它。1985年,就该雕塑的命运,举行了一次公开审理,法官裁定铲除。1989年雕塑被裁碎,送到废铁厂。作为艺术作品,倾斜的弧毫无疑问应该存在,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来说,这件雕塑造成生活不便,应该移除。二者所基于的元语言组分不同,无法互相取消,面对一件艺术品做漩涡式的评价,法官不得不舍弃一说。
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对自己的作品都感到无所适从:黑人女性一直面临性属与种族两个问题,黑人女性应该先是“黑人”还是先是“女性”?作为黑人似乎有义务维护男性形象,作为女性又应该揭发、反抗黑人男性的虐待。从黑人女性来看,书写黑人女性经历则是她们的首要任务,讲述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不公对待,为自己争取权利非常重要,而这一行为则被男性认为是有损黑人男性形象,出卖了黑人民族,不利于黑人整体形象。莫里森对此解释漩涡很感困惑,她的诺奖庆功宴没有请任何黑人男作家参加。
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复杂化,解释漩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而“泛艺术化”也在推动漩涡,复杂解释开始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当代社会最常见的商品设计艺术化,经常导致解释漩涡。例如现在有一种衣服既可以正着穿,也可以反着穿,一衣双穿,没有“里”“外”之分。正着穿时的“里”恰好是反着穿时的“外”,反之亦然。我们在使用或欣赏这件衣服时,必须把看到的一面既作“里”又作“外”。
许多时尚名牌,设计返回粗糙外表路线,例如爱马仕的粗棒针毛衣,路易·威登的红蓝行李编织袋,卡尔文·克莱恩的布鞋。顾客觉得太像粗棒针毛衣、红蓝编织袋、布鞋,觉得与村妇织的毛衣、民工用的编织袋、老人穿的千层底布鞋,会认为这是土货。但在看到毛衣上的爱马仕logo、编织袋上的LV商标时,又会觉得这些时尚大牌不会犯傻,这些设计必定是在开启时尚新潮流,于是这些追求名牌者,落进解释漩涡之中。
支付宝推出的微博转发“中国锦鲤”活动,接受主体大众,尤其是比较有思想的学生群,对它产生了既肯定又否定,难以取舍的解释漩涡。一方面,他们认为参加转发锦鲤活动可以适当缓解焦虑,让内心获得片刻的安全感,所以认为转发锦鲤活动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他们觉得这是商家营销的惯用伎俩,转发锦鲤会被商家利用,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活动,使其本身的目的陷入两难。
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内心纠结可以说在生活中随时发生。虽然解释漩涡必须发生于“同一人的同一次解释活动”之中,这个条件似乎很苛刻,实际上这个条件也适用于反讽与悖论这样有主副义的意义方式,只是一般论者没有讨论到这个条件而已。
五、解释漩涡产生的原因
对符号文本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要依靠一定的解释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符码。符码的集合称为“元语言”。符码就相当于一本词典中的词条,或密码本中的对应理解,而元语言可以比喻为全本词典,或整个密码体系。旨在解释个别符号的符码,必须组成覆盖全域的元语言,才能保证翻译—解释的顺利进行。
符号意义的可解释性,就是可以用另一种符号体系来替代,比如中文可以翻译成英语,这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完成意义转换的关键是元语言(可以比成一本词典),其保证了文本意义的“可翻译性”。任何“翻译”,不管是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还是翻译成另一种体裁,都靠一个完整的元语言在背后支撑。
元语言问题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元语言是分层控制的。1920年罗素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指出层控是元语言的根本品质:“每种语言,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但是可以有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也就是说元语言可以分成多层,每一层无法自我说明,只能把自己变成对象语,靠上一层元语言(即元元语言)解释它。波兰元语言理论家塔斯基认为,上层元语言,总是比对象语“本质上更丰富”,也就是解释能力越强。
既然每一层元语言都是一个整体,其结构无法自我说明,必须用上一层的元语言来解释,那么,每个层次的元语言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内部就不会有冲突。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玄,中国古人却深明层次分割之理。明末董说的小说《西游补》,第四回孙行者入小月王万镜楼,镜中见故人刘伯钦,慌忙长揖,问:“为何同在这里?”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被元语言分割的层次,在意义上互相是独立的。
在解释活动中,各人所用元语言不同,解释就会不同。哪怕同一个或同一批人,元语言发生变化,前后解释就不同。本文要问的是:如果情况不是罗素描述的那样,如果每一层的元语言并不是一个整体,同一个解释中使用的元语言,组成的方式是否可以多元?在同一次解释努力中,如果使用了不同组成方式的元语言,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元语言的不同组合产生冲突的意义(相当于用了几种不同版本的词典),这些不同的意义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些解释同样有效,此时最后期盼的解释以什么形态出现?如果解释背后的元语言集合,由各种不同因素组成,那么,组成解释中的元语言因素来自何处?本文所说的“解释漩涡”,即是这种同层次不同组合的元语言冲突。
仔细检查符号表意—解释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参与构筑解释所需的元语言集合。因此,大致上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分成三类: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解释者本人的“能力—经验元语言”以及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
第一种元语言,符号文本内有自携元语言,也就是说文本本身,总带着某些指示如何解读的因素,这是雅各布森首先提出来的。当符号侧重于符码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烈的“元语言倾向”(metalingual),即符号文本提供线索应当如何解释自身。往往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好好听着”这样的指示符号来提醒。文本的体裁、风格、标题等元素,也是明显的自携的元语言。元语言不一定处在文本的上一层次,符号文本往往提出了对自身的解释方法,这一点,是雅各布森对符号学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文本固然是解释的对象,但也构筑了一部分解释所需的元语言,且为此提供的组分还相当重要。
例如,一个文本本身就表明了是“一首古典诗”,“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这就成了影响解释的重大因素:当作诗来读,与当作新闻报道来读,解释方法极端不同。故事影片中有恐怖场面,纪录片或电视“现场直播”中也会有血腥暴力场面。哪怕文本表现场面相同,体裁要求两种不同的解释。每一种体裁对解读方式要求非常具体,甚至同样文本,例如《诗经》,当作文学读,与当作“多识鸟兽鱼虫之名”的教科书来读,不同的体裁要求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符号文本中,处处可见自携元语言的标记,指导应该如何解释自己。拿比喻来说,比喻的“相似”,经常是一种元语言自我设定。也就是说,语句中有“像”“似”这样的词,才造成比喻的强制解释。承认系词的力量,比喻的解释就出现了张力。再例如小说和电影叙述中的“前因后果”:应当说在现实中,前面出现的不一定为后面紧接着出现事件之因,单数叙述文本的构成,强制时序在解释中变成因果。
第二种元语言,能力—经验元语言,来自解释者本人的经历,他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解释活动的沉淀。这些都参与构成他的能力—经验元语言。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实践,精神分析强调的幼时成长经验,布迪厄所说的进入文学场的人所携带的“习性”与“素质”,都给这一次的解释提供元语言。可以说,这就是克里斯蒂娃讨论的“文本间性”的个人化,只是发生在解释者的头脑之中。
也有一些解释能力与生俱来,例如孟子说的人性本有的道德能力如恻隐之心,康德阐释的一系列先验范畴,心理学指出的一些人类先天能力,等等,都汇合进入解释者的元语言能力。这些先天能力不由解释者控制,一旦面对解释需要,有关因素就会冒出来出来,与上面讨论的社会文化经验,汇聚结合成一个可用的元语言组合。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文本,第一次无法理解明白,需重读方见妙处。理法泰尔称这种现象为“追溯阅读”(retroactive reading),“我应当强调再强调,这种初次阅读的障碍,正是符号意义的指南,是通向更高的系统上意义的钥匙,因为读者明白了这是复杂结构的一部分”。理法泰尔指出:“不用说,这种于理不通引人注目,为狂欢理解的洪水打开了闸门”。
能力—经验元语言因素,还包括感情与信仰。一般不称之为“能力”,但是在理性解释的背后,情感或信仰起了很强大的作用。这些因素对解释影响能力极强,经常超过理智的能力,尤其能使解释者坚定维护他的解释之有效性。利科说:“为了理解而信仰,为了信仰而理解,这是现象学的箴言……就是信仰和理解的解释学循环。”信仰为解释者提供的,实为一种强有力的“能力—经验元语言”。上文中举出的许多例子,很多是信仰导致的“应该如此想”的问题。
应当说明,元语言“能力”是接收者自己的感觉,并不一定可以客观测定。不少人相信自己有关于、股票、期货、金价之类的预测能力,有对灾难或福分的预感能力。只要他自己对自己能做出有理由的解释,就是他的能力元语言。
而第三种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解释符码组成的最重要来源,它们是在解释实践发生时,文本使用环境造成的元语言。也就是文本与社会的关联方式,要求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处理方式。文本处于不同的社会场合,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使用同样符号文本,意义可以完全不同。“传达集团”的变化,可以使解释整个改变。军队、青年人社群、黑社会,各有一套独特的表意方式。《水浒传》中上梁山,须杀人作“投名状”,在其他社会各界完全不能用;军官发出的命令,须在军营内、战场上,才有其权威,语境是解释意义生成的条件。
因此,支持每次解释的元语言组合,其构成虽然相当复杂,但这些具体因素并不神秘。解释者(一个人或一批人)面对符号文本,采用的元语言,是每次解释时自觉不自觉地用各种因素配制起来的。像做菜放调料一样,似乎有配方可遵循,但是解释者可以临时机变。本文试图说清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元语言组合的可调节性。这样一来,元语言集合的组成方式,就很有可能在“内部”发生冲突,就会出现一个解释不能取消另一个解释,两个相反的解释同时有效的漩涡。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