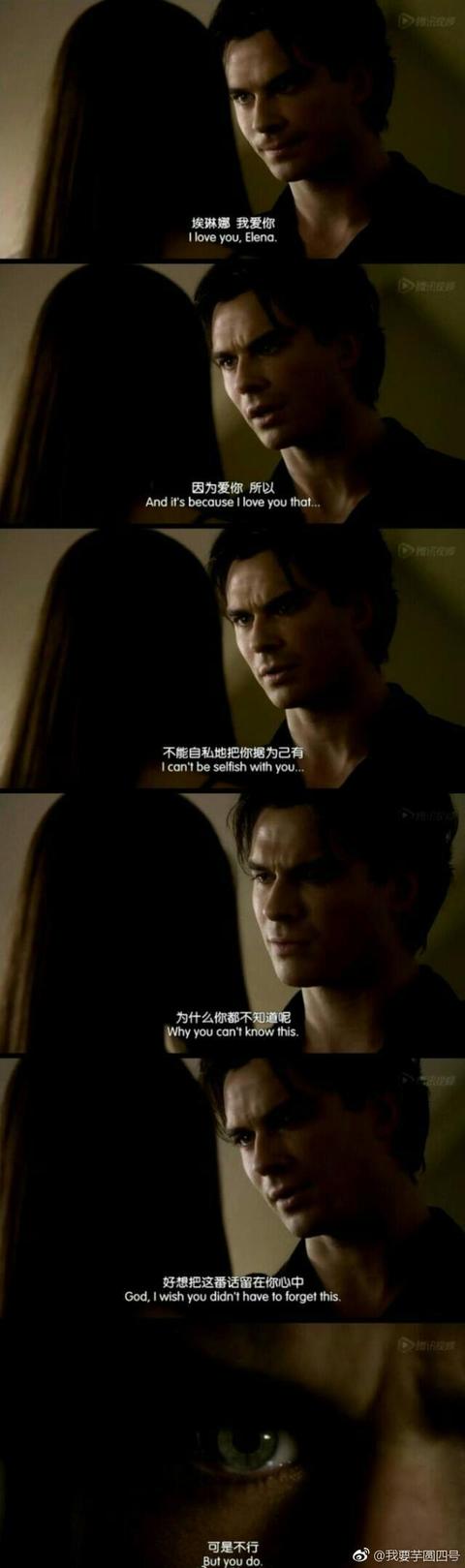“我要走了。”小小的女孩对我说。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我们全家都要走了,也许去东边,也许去西边,反正我们不在这里了。”小小的女孩故作深沉的说着。可是语气却掩藏不住的兴奋。
“哦……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
“你放心,我会写信给你的。”女孩对着我的肩膀拍了一下,一脸的意气风发。
我重重的点头,很大声地应了一声‘好’心里瞬间开心了不少。
女孩是我儿时的玩伴,你要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还真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一直都是叫她小唐妹。小唐妹很开朗,她有许多一起玩的小伙伴,我只是其中一个。而我生来内向不爱说话,我的小伙伴只有她一个。所以她走的那天,许多小孩都围在她身边跟她道别,而我不愿意挤进去,就去了我家旁边的小卖部,那里是可以看到她又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太孤零的地方。
小卖部以长身的格局挨着我家。简朴而陈旧的老房子总是散发着一股发霉闷气的味道。店面又窄又长,只够放一个冰柜一张玻璃柜台和一台电视,还有几张四角凳子。
往年夏天,附近的小孩都爱集中在这里买上一些山楂、开口笑、冰棍啊什么之类的,边看着动画片边吃零食。只有今天,店里空荡荡的,只剩周叔和他的老婆在看电视。
“周叔,我要一包干脆面。”我把五毛钱豪气地拍在玻璃柜台上。
周叔应了一声,笑呵呵的穿上塑料拖鞋,背着身像变魔术一样,把一包干脆面递给我。周叔的手上有厚厚的茧子,纹路又深又杂,指尖的死皮翘起,划过我的手背带来一阵刺痛感。我瑟缩的样子引得他哈哈大笑,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把一张小凳子搬到外面,背朝太阳坐下,拆开干脆面的袋子,把调料包拆开洒到面饼上,面朝小唐妹的家,一口一口的咬碎嚼进肚子。
今天小唐妹还穿上了新衣服,被一群小孩围着就像个小公主一样。她看见了我,开心地朝我招招手。
“你的小伙伴要走了,你咋不找她说说话?”周叔也搬了张凳子在我身边坐下。周叔身上有一种气味,那是一种常年熏着的中药味,我不喜欢,却又不排斥。
我摇摇头,心里闷得很,即使美味的干脆面也不能抚平我因唯一的朋友离去而带来的忧伤感。
亲爱的小唐妹,你走了还会记得我么?
周叔伸手在我的头顶上重重的揉了两下。从地上的倒影上看,我头上的杂毛像炸了一样,往四周散开,长短不一,看起来甚是恐怖。
我用手抚了一下那些杂毛。软软痒痒的,抚过去了又再冒出来,就这么一分钟,我似乎忘了小唐妹,就专注于我的杂毛所带来的乐趣。
“喂——”小唐妹举高双臂,站在皮卡车边跟我招手。
我不知怎地,突然生出了一股气,别扭地依然坐着,和她的激动截然相反。
“再见了——”
我没有回应,依然嚼着我的干脆面,香辣的味道入了口突然没了味道。那时七岁的我,第一次尝到了离别所带来的苦涩。
“没事的,这个朋友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只要你心里一直记着她。”周叔找了一把梳子过来替我梳直头发。
他总是这样,喜欢把我的头发弄乱然后又重新给我捋直了,梳着各种各样的辫子,比我妈妈梳得还好。
“可是别人不愿意跟我玩。”我不爱说话,常常喜欢一个人待着玩,也喜欢和别人一起玩,但是他们总说我怪。我不知道怪是什么,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玩么?只有小唐妹爱带着我玩,小唐妹走了,我也就没有朋友了。
周叔把我转过来,硕大的粗手捏着我的两颊,混浊的眼睛闪着某种我看不懂的光芒,可我知道那是好的。
“你可以来找周叔玩。”
“别人也不找你玩么?”
周叔哈哈地笑了起来,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那个下午周叔陪我玩了许多游戏,开着我喜欢的动画片,还请我吃了冰棍,我很开心,即使没有小唐妹,依然有人愿意和我玩。
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妈妈一脸严肃的看着我,我知道她打麻将肯定又输钱了。她的情绪很分明,通常打麻将输了回家看什么都要骂上两句,嘴巴翘着能挂酱油,赢钱了就算在她头上拔两根头发,她也是笑呵呵的。这种情绪化的性格在我的成长里带来很深的影响。
妈妈扯着周叔给我梳的小辫子,一脸的嫌弃,嘴上骂骂咧咧的说着让我不要再去小卖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带着我玩,和很多时候一样,我习惯了不去问为什么,这可能是源于一种自卑,也许也是一种保护,保护自己那颗敏感易碎的心灵。
“你听到没有!”妈妈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我郁闷地点点头,下午美好的心情荡然无存。原来周叔和我是一样的,都是被勒令不能一起玩的人,我心中对周叔又亲近了一分。
周叔是前两年搬过来的,他家只有三口人,父亲妻子和他。周爷爷有帕金森,每次卖东西手抖得厉害,总要抓几次才能拿起来,调皮的小孩总是学着他的样子哈哈大笑,周爷爷也不生气,总是笑呵呵的,就和周叔一样,仿佛他们生来就没有脾气似的。
周叔的老婆姓庞,是个残疾人。脸上无肉,因为常年不晒太阳的原因,总是一脸惨白。她的眼睛很大,常常睁着一双大眼直白的看着我,嘴上咿咿呀呀地在说着什么,我听不懂的时候总是嫌弃她。周叔告诉我,年轻时候的庞姨也是一个漂亮姑娘,只不过出了一点事故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庞姨年轻的时候喜欢赌博,被追债上门才导致的中风瘫痪,最后连话也不会说了。
周叔对庞姨很好,我每天上学放学总能看到周叔给庞姨按摩手脚,喂饭聊天。我心里是愿意亲近周叔的,可是我没想到有一天却是我伤害了这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
那天我在小卖部玩玻璃球,用力过猛把玻璃球弹进他们居住的地方,我跑进去捡,不小心又把玻璃球推向更里面的地方。我的对声音很敏感,即使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夹杂在电视声里混着,我依然听出了是正对着我的房间传出来的,那声音似痛苦又似欢愉。
我忍不住好奇往前一探究竟。周叔有一个大大的肚子,往常邻里的小伙伴们都爱拍着他的肚皮,像拍西瓜一样‘砰砰’作响,而我喜欢用脑袋顶着他的肚皮和他一来一往的‘较量’,这渐渐就成了小伙伴们中的一项娱乐活动。我曾经还为自己发明了这个游戏而沾沾自喜,然而现在我讨厌这个游戏。
周叔用他的肚子摧毁了我童年仅有的那点回忆,用他的双手摧毁了我对长发的喜爱,用他的脸摧毁了我对善意的分辨。我尖叫一声,哭了出来。
因为我的一声尖叫,周叔提着裤子蹲着哄着哭泣的我的画面深深刻在每一个冲进来的人的脑海。任周叔怎么解释,没有人相信他,而这个不相信也是因为我的不做声。
我讨厌周叔,那张扭曲涨红的嘴脸像极了我讨厌的老师,欺负我的同学。我报复性的不愿意说任何话,不管父母怎么问,我始终不开口。我不知道我的不开口会带来什么后果,直到警察过来把周叔带走。
“看不出他还是这种人哦,真是个禽兽……”
“你看他老婆躺在床上那么久,都不知道憋了多少坏心眼……”
“那也不能对孩子下手啊……”
“活该让他坐牢……”
邻里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躲着我来说。我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我害怕了,终于开口对警察说了事情的经过。很快,周叔被放了出来。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虽然周叔被证实了清白,但是流言蜚语并没有放过他,所有人都在背后嗤笑指指点点,包括我。其实事件结束之后,周叔曾努力地想回复到以前邻里的关系,他努力组局打扑克,送很多零食给小孩们,所有人接受着他的讨好,却依然没有改变什么。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叔是在晚上,我知道他想和我说话,也许是我一脸的防备另他退却,他的嘴巴嚅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远走的背景像泄了气的皮球,驮着背没了精气神,我心里不是滋味,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传来周叔搬家的消息。曾经热闹的小卖部再没有欢声笑语,大门紧闭灰尘满天,没有人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小唐妹给我来过两封信,后来就不再给我写了,我以为她没收到,又寄了很多封信之后才明白我们的友情已经结束了。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偶尔和洋娃娃说话,偶尔听到邻里说没地方待着闲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