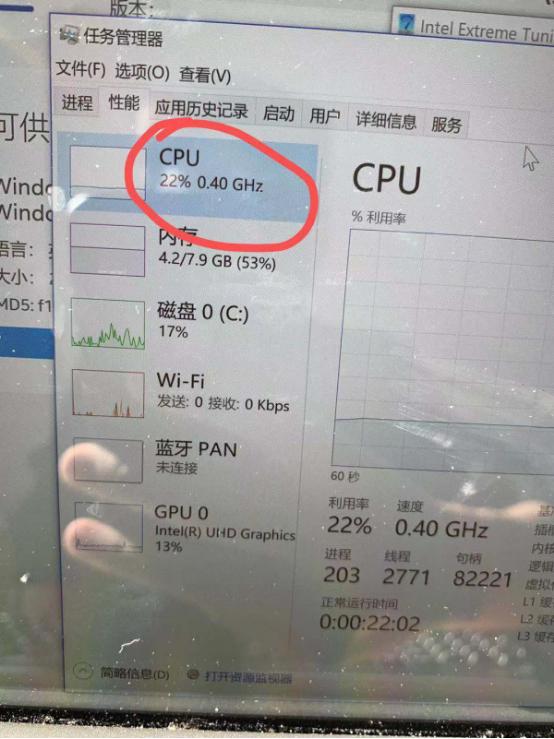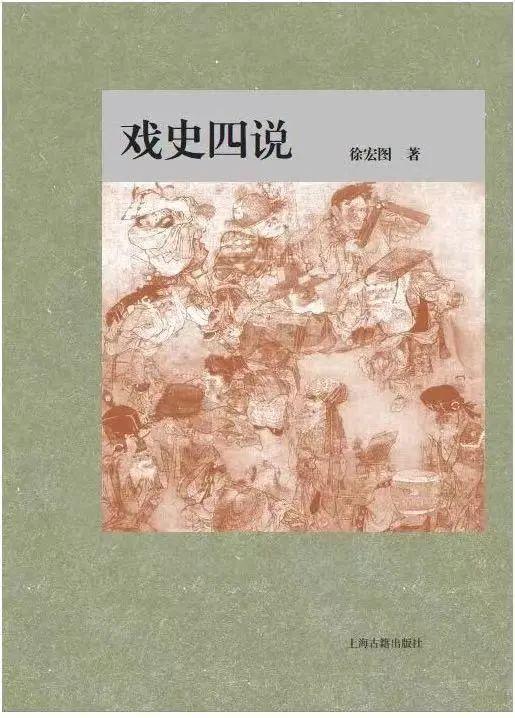
《戏史四说》
徐宏图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介绍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最早的成熟形式之一。昆曲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仪式剧既具有宗教仪式的性质,又具有中国戏曲的特征,是介乎仪式与戏曲之间的艺术形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稿是作者多年以来对于以上几种戏剧起源、发展、具体剧目、相关人物等内容所进行的研究总结。考察了南戏的滥觞、诞生、分期、遗存等;昆曲的入京、入浙及张宗祥、庄一拂、周瑞深、黄源、徐朔方等人物;傩戏的起源、流向及其在浙江的遗踪等问题。
作者简介
徐宏图,男,1945年3月生,浙江平阳县人。先后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编委兼责编、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现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戏曲史论研究,已出版专著《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浙江戏曲史》等30多种,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分别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前言摘录
我研究戏曲已半个多世纪了,1984年之前为业余研究,从是年开始因调入浙江省文化厅主持的《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担任编委兼“责编”便转入专业研究。从此,不仅使我有机会考察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历史与现状,如下剧团体验演艺生活、接触编导与演员、观看各剧种的演出等,而且还收集了大量的戏曲文物与资料,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我的大部分专著与论文,均离不开于戏曲志编纂期间搜集的史料。其中已发表的200多篇论文散见于海内外各种杂志与报纸,为了便于读者查阅,现选择30篇,分为“说南戏”“说昆剧”“说元杂剧”“说仪式剧”四编结集出版,末附已发表的著述简目。现先将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略说如下:
关于南戏,有四点拙见:一是针对王国维认为南戏的诞生与宋杂剧“无涉”的论点,提出南戏是由温州的“里巷歌谣”吸收诸多艺术成分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宋杂剧的影响尤大,已在“自报家门”“脚色行当”“服饰”“剧目”以及综合表演等五个方面为南戏的诞生奠定了一些基础,可见,二者从体制上说可谓“无涉”,但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方面说则是紧密关联的。二是首次对南戏的发展作了分期,共分为五期:北宋宣和前为诞生期,南宋光宗朝为成熟期,光宗朝至元末为鼎盛期,元末至明嘉靖年间为演进期,明嘉靖至清初为传奇期。传奇时期的南戏依然存在,从而颠覆了“南戏只存在于宋元至明初”的旧说。三是提出“传奇”是剧本形式而不是剧种的观点。认为“传奇”诞生之前,南戏的剧本形式称“戏文”,诞生之后称“传奇”,二者并无质的区别,只不过前者大多为无名氏的民间作品,后者则是名公文士之作,故事更长、情节更离奇而已。四是指出南戏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已有史料的辑佚、汇编、集成等不断地重复中,更要深入田野调查,调查南戏在民间的遗传,包括作家、作品、表演艺术等。尤其是剧目,曾大量地被高、昆、乱、徽等各大声腔剧种所改编或移植,一直在民间演出。详见拙著《南戏遗存考论》。
关于昆曲也有四点:一是昆曲割不断与吴歌的血缘关系,包括语音相承、音乐相继、题材相袭诸方面。详见拙作《昆山腔与吴歌的关系》。二是“草昆”之说无法成立。首先,昆剧在草台与庙台或城镇戏台演出的剧目及规格没有两样,不能因为在“草台”演出、具有草根性就称它为“草昆”,在其他戏台演出的则称为“正昆”。凡民间戏曲均曾在草台演出过,京、徽亦不例外,何不也称京剧、徽戏为“草京”“草徽”呢?这显然不合情理。其次,所谓唱腔“不正规”“不纯粹”,这是一种静止眼光的说法,须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水磨昆腔从昆山流向外埠之后,因受当地语言、欣赏习俗等因素影响而出现的某些变化,如字音直吐,不作反切;板眼紧促,难以舒缓等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流入地观众的审美需求。把这种必要的变化而斥之为“不正规”“不纯粹”,甚至怀疑其“花”的本质而贬其为“草”,不仅不慎重,而且不科学。第三,“与其他声腔剧种同台演出”,这更不能成为“草昆”的理由。众所周知,清中叶乱弹迅速兴起,昆曲受到冲击,逐渐失去优势,至晚清即不得不与乱弹、高腔、徽戏合班同台演出。同台演出只是权宜之计,演出时绝没有被对方所同化,依然追随“正昆”规格,何由谓之“草昆”?详见拙作《浙江诸昆非“草”皆“花”》。三是首提“业余曲社是昆曲的半壁江山”的观点,在昆曲发展史上,曲社一方面为昆班培养和输送人才,另一方面又接纳了昆班艺人担任教师,为昆剧事业立下汗马之功。在昆剧面临失传的困境时,这种半边天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例如,当国风苏昆剧团在江浙一带苦苦挣扎之时,杭州建德县新叶村昆班却进入四处被抢着邀演的时期,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这是昆曲发展史上一个相对当可喜的现象。详见拙作《业余曲社的半壁江山》。四是对“京昆不挡”的旧说作了补证。旧说只从京剧演员好学、多艺、能兼演昆剧的角度加以褒扬,笔者则从昆曲独尊、京盛昆衰、拜昆为师三方面予以论证。同时指出“京昆不挡”是我国京、昆戏曲发展史上此消彼长而又同舟共济的产物,它既造就了一代昆乱兼擅、文武不挡的京剧名家,又保存了一度衰落的昆曲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在中国戏曲史上写下颇具特色的一页,理应引起戏曲界的重视。详见拙作《“京昆不挡”补说》。
关于元杂剧有三点:一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是南戏而不是元杂剧。因为确定戏曲的成熟标志,不能单从“文学性”去判断,更应该从“演剧性”去衡量,元杂剧虽然在文学性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就,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评价的“为一代之绝作”,然而在演剧性方面,远不如先出于它的南戏成熟。例如在演唱方式上,元杂剧的每一折戏只允许一种脚色放唱,凡由“正末”唱的,称“末本”,凡由“正旦”唱的,称“旦本”,就大不如南戏各种脚色都可以唱,或独唱,或对唱,或合唱,或轮唱,完全不受约束来得成熟。二是元杂剧虽然诞生在北方,先在北方崭露头角,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大家,被学术界称为第一个繁荣期。然而,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元朝一统天下,就很快地传播到南方,关汉卿、珠帘秀等名家名伶纷纷来到杭州,杭州成了创作、演出、研究三大中心,其繁盛或超过大都时期。三是分别记录、研究元杂剧作家与演员的《录鬼簿》与《青楼集》堪称是元代戏曲论著的“双璧”。前者为钟嗣成著,记录约150位作家的事迹,后者为夏庭芝著,记录约150名演员主要是坤角的身世与演艺,均为空前绝后之作,必须更加深入研究。详见拙著《青楼集笺注》。
关于仪式剧有四点:一是提出“内坛法事外台戏”的观点。凡举办祭祀活动并演出仪式剧,均有内坛与外台两个区间,内坛由道或释主持法事仪式,参与者均为头家与信徒;外台则请戏班演出与内坛相关的剧目,如傩戏、目连戏之类,以招待广大观众,既娱神又娱人,戏台的对面设有神位,故鲁迅《女吊》才说:“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戏,不过叨光。”详见拙著《浙江目连戏资料汇编·前言》。二是仪式剧的发展历经“两大蜕变”:首先,由仪式蜕变为仪式剧,如目连戏即蜕变于中元节内坛诵念的《佛说盂兰盆经》,又称《目连救母经》,叙述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目连十殿救母的故事。他如傩戏、醒感戏、孟姜戏等无不如此。其次,由仪式剧蜕变为普通戏剧,如永康醒感戏,原先只能在“庆忏鸿楼大会”(俗称“翻九楼”)道场中演出,为内坛服务,演出时尚有种种限制,如场景必设地府、十殿、油锅、血湖等,后来经过破除“迷信”,脱离仪式,蜕变为普通戏曲,原先的种种限制统统抛弃,终于成为本省十大高腔剧种之一。(详见拙作《永康醒感戏初探》)绍兴孟姜戏的演变过程与永康醒感戏相似,有“日翻九楼,夜演孟姜”之称,蜕变于“太平会”仪式,再度蜕变即成为高腔孟姜戏。(详见拙作《日翻九楼,夜演孟姜》)傩戏亦大致如此,从傩仪到傩舞再到傩戏的蜕化过程。(详见拙著《浙江傩戏资料汇编·前言》)。三是对任二北、郑振铎的“目连戏传自印度”的观点提出质疑,阐述了“中国目连戏非传自印度”观点。同时阐明了目连戏诞生的“经文—变文—戏文”的三大历程:经文,即西晋初年三藏竺法护据梵文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为目连戏的故事情节提供依据;变文,即《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目连戏的演唱奠定基础;戏文,由于戏剧所必须具备的故事情节及表演形式均已成熟,目连救母这个故事便从变文中脱胎而出,首先以宋杂剧《目连救母》进入戏剧领域,再进一步即成为戏文或院本《打青提》等,至明代郑之珍据民间大量传本编为《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详见拙作《中国目连戏非传自印度辨》)四是提出“农村的戏曲靠庙会”的观点,这是我长期关注并参加各种庙会的亲身体会。首先,庙会为戏剧提供演出场所;其次,庙会为戏剧培养了大量的观众,庙会戏剧既不同于只为少数人演出的堂会戏,也不同于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演出的剧场戏,而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演剧活动;第三,庙会还是戏剧的避风港,在封建时代,戏剧经常要受到统治者的“榜禁”,只有托为“禳灾赛祷”,才能躲过此灾。反之,庙会也离不开戏曲,它必须借戏剧以娱神(人),因此,各地庙会都有自己基本固定的戏班,不同的庙会要求演出不同的剧目,并通“斗台”等形式培养观众的兴趣与水平。(详见拙作《戏剧的生存与庙会》)
我治学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独辟小径,不与人撞车”。王粲诗云“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拙作无论内容或书名均有点冷僻,如戏曲类的《青楼集笺注》《戏曲优伶史》《南戏遗存考论》;宗教类的《平阳东岳观道教音乐》《磐安县树德堂道坛科仪本》等;民俗类的《仰头村的西方乐》《深泽村的炼火仪式》等,均为前人所未写(详见拙作《独辟小径的收获》)。二是重“田野调查”,即前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应邀参加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主持的“中国仪式剧研究计划”及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主诗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密切相关,使我有机会接触一批西方人类学家,向他们学习田野调查的概念、意义、方法等,并学以致用,深入民间调查,撰写了诸如《绍兴孟姜女》《永康醒感戏》《杭州抱朴道院道教音乐》等著作与论文。其好处是:写前人所未写,道前人所未道,无论专著或论文,均可避免撞车与雷同,给人以新感觉。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徐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