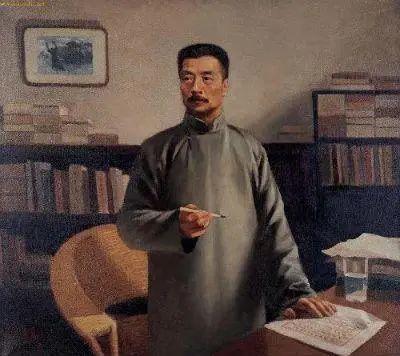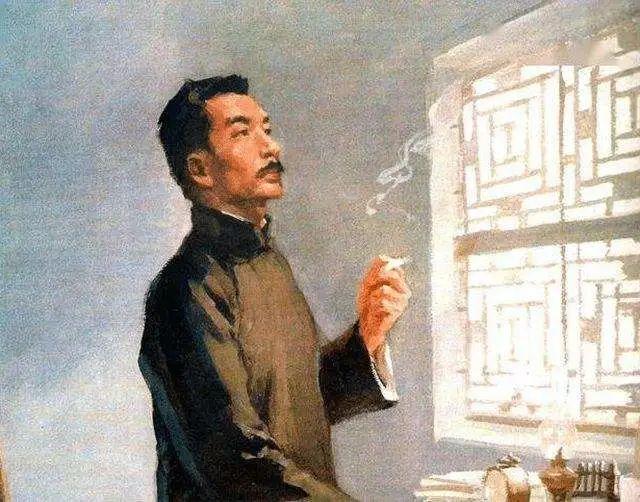关注 ,让诗歌点亮生活

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参加第4次全国青年作家会议、诗刊社第9届“青春诗会”,2010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花城》《十月》《散文》《随笔》等刊物,组诗《东方大道:陕北》获1991年《诗刊》年度奖,中篇散文《马坊书》《读莫扎特与忆乡村》荣登《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年度排行榜。已出版《长安书》《秦岭书》《马坊书》等诗歌、散文集十余部及四卷本《过山河记》。作品荣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等奖项。你的文字是一副中药
一位小个子的人。
你消瘦的身躯,能在消瘦的大地上,留下怎样消瘦的影子,只有你知道。
你也知道,天空会亮。天空会从故乡鲁镇,带着闰土的目光,会有些忧郁地亮。你也带着自己消瘦的影子,朝向北方走去。
激扬山河。
你的文字,是你下给病中的大地,一副很猛的中药。
你也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病中的大地,也像一片可以从很深的地下,烧毁一切腐朽的野草。在你的影子里,那些倒下的青年人,可以收到,死亡的安魂书。
那些害怕你的人,却想着怎么,踩死你的影子。
带着身上,那些散发在文字里的药味,你把黑白分明的影子,带到鲁镇以外的大地上。
真正的泪水是红的
跪在父亲,安睡的坟前。你看见流出天空的那些云朵,全被死在母亲眼睛里的,泪水打湿。
你是一个,见不得一滴泪水的人。
你以为人间的伤逝,会让所有死去的文字,不再腐朽下去。因为你见过的血迹太多。多到泪水,不能擦拭。也多到泪水,猩红如暗夜里的一把残火,在痛苦者的脸上,像血一样。
世人不知,你在文字之外,把母亲为你流过的每一滴苦涩的泪,都积攒起来。时间让它,凝固成一颗血一样的琥珀。也是时间,让它在你绞痛的心里,反复打磨,那些带着身上剩余的温度,点燃地火的文字。
你在母亲的泪水里,看见母亲的伤逝,和你看见的人间的伤逝,一样深重,也一样猩红。
因为吞下你的文字
你的心里,烙满了血字。你的心里,也烙满了悔恨。
因为吞下,你的文字,那么多有血性的年轻人,赶在黑暗里,扛着青春赴死。你蘸着血水,诉说给长夜,那些揪心的话语,点燃他们身边的野草。子弹穿过胸膛,你的文字,成了死亡者,曾经读过的祭文。
坐在暗夜里,你怀疑过,这些蘸着,很多血水的文字。
有时候,会不会是一剂中药中的毒药?那些吞下它们的人,像点燃了疯长在心里的野草。天空,没有照亮如山的尸骨里,成了没有坟墓的新鬼。
甩掉手中的笔,站起的你,也想被自己的文字埋葬。
需要你坐在椅子上
一把放在,暗夜里的椅子。
一把坐着,大先生的椅子。
坐在一把,像生铁一样冰冷,也一样炙热的椅子上,你的血液动荡。你的骨头,支撑着你的身子,像在给含恨的笔墨,铺开带有温度的纸张。你想用研磨在身体的伤痛里,有如中药的一些文字,最先救救孩子。
一支带血,燃烧在暗夜里的烟卷,闻着你种植在文字里,那些越来越困难的呼吸,很想终结,这些不眠的夜晚。
一件御寒的毛衣,也被你犀利的文字磨破。
不要起身。在暗夜里,人们需要你坐在椅子上。
一把活在,文字深处的椅子。
一把安放,国家精神的椅子。
欠被毁的朱安一个笑
你和朱安,都在各自的暗夜里,不安地生活着。
很多时候,当你脸上的笑,通过你的文字,燃烧着散发到很多人的身上,那个叫朱安的女人,她的心里一直很冷,你却不知道。
她的这辈子,过得好冷。
她没有在文字里,看见过你。她在你深邃的眼睛里,看见了婚姻里的你,就是一块,结了的冰。如果她能真实地取下,你看见她时,冻在脸上的笑,她就会把它挂在家里的墙上,死心塌地地陪着你,直至死去。
一生捍卫自己,你不欠谁。
就欠被毁的朱安一个笑。
娶的是母亲的眼泪
可以想象:为了迎娶朱安,你把在东京断然剪掉了的辫子,换成假的,再次戴上。也可以想象:为了弥补自己,没有放脚的过错,朱安给粽子似的小脚,穿上好大的绣花鞋。
铁一样的心里,装着铁一样意志的你。
要在活人和死人的眼皮下,把这处乡戏演完。
这处婚姻的乡戏,让最恨地狱的你,为一个活着的女人,制造了一座可怕的地狱。你的先知先觉,在不能背叛母亲的眼泪的时候,让那支握在手里的,春秋之笔,也变得愚钝。
多年以后的今天,站在一场戏里,你才冷冷地承认:
娶的不是新娘,娶的是母亲的眼泪。
你也有沉默的时候
你也有沉默的时候。
带着一身伤痕,你后退着。后退到死去的,青年们冰冷的坟墓里。
你沉默着。不是你看见了,太多的血,抹杀了他们青春的面庞。也不是你听见了,他们挣扎在你的文字里,不忘按照呐喊的节奏,留下的最后的呼吸。
你沉默着。是你看见了,他们中一些暂时活着的人,突然长出了狼的牙齿,石头的心脏。你也看见了,他们从身上抹去,穷人的痛苦,穷人的眼泪。
你也有沉默的时候。呐喊,是对你最大的误读。但你不会,背叛最后一滴血。
那是留给,青年的粮食。
只想逃回到坟墓里
这是一个怎样的天堂?
你的巨幅画像下,世界和你,一样消瘦地坐着。
这是拯救了人间的那个天堂?坐在离地狱并不远的地方,你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被他们请进来的你。坐在这里,你需要重读,很多人的面孔:那些被你怜悯的小人物,那些被你痛恨的大人物。
还有那些,忙着脱胎换骨的,一群读书人。
他们让你,看到一个走了大样的天堂。
你想起身,一个人逃离。带着身上剩余不多的力气,只想逃回到坟墓里。那样,你就会盯住所有的罪孽,也把虚假的天堂推倒。
一捆血色的绳子
你用文字,热敷大地的时候,也想用一捆血色的绳子,在大地上,为你熟悉的闰土,圈出一片,你以为安全的地方。
那时的大地,过于寒冷。
那时的闰土,听不懂你在啼血呐喊什么。但你熟悉闰土的身世,他最大的危亡,不是身体能否经受得住寒冷,而是暴虐者要划开他的肌肤,取出一把,消瘦的骨头。
多年以后,我能想见,你用一捆血色的绳子,隔开闰土和暴虐者时,那是怎样残酷的场面。你只有咬紧牙齿,划破自己的手指,让身体里剩余的血,滴在那捆绳子上。
而抵挡遍地刀刃,只有让血,不停地燃烧。
你的那些,热敷大地的文字,背在后来人身上,是一捆血色的绳子。
那个年代,让你活得像个古人。
结绳记事,用的却是自己的血。
你的血要流到什么时候
大哥,你的血要流到什么时候?
叫你一声,一片山河就破碎了。
你就是那个,不想与弟弟反目成仇的大哥。你就是那个,哭着分手之后,要记住闰土一生的大哥。天亮了,你还没有写完,蘸在笔尖上,那些很寒冷的夜色。也是弟弟,看见你写下的文字,像你流出的血,才这么惊呼。
这一声惊呼,或许只有坐到天亮了的你,没有听见。
因为那时的困倦,带着没有写出的文字,歇在笔尖上。
你不会知道,在弟弟知堂看云的眼里,你这是流着身上的血,在为孤苦的人挑水、劈柴、做饭,你这是在毁灭自己。
大哥,合上日记的弟弟喊你。
想着闰土的你,却没有听见。
她没有力气为你赴死
不是她,没有想到过死。也不是她,怕对不住你。
她活着,是她的过错。她死去,是对你的刑罚。
跳在一个人的暗夜里,她心里的冷,没有边际。
她早想以一位女人的,清净之身,为你死去。
如果问罪于你的世界,真的需要,一个祭品。
只是心里的,冷,让她走不到,鬼魂那里去。
朱安,很像一个渐冻人,她没有力气,为你赴死。
闰土的皱纹和眼泪
多年以后,你所看见的闰土,混合着一脸皱纹和眼泪。
他被时间,带着疼痛,重新纺织。
那些年,他能真实地挂在这张脸上的,就是这些皱纹和眼泪。迎面在故乡的风里,从外到里,这些切割他的冷兵器,触碰到的,都是一个人的悲伤,一个人的冷漠。怀揣不安的中国,你像看到了,所有人的下场。
借着光亮,你要看清,木头一样的闰土。
你要苍天,清醒地回答:是谁让他活得这样悲伤?这样冷漠?坐在长夜里,你也看着自己,不知怎样安慰他的皱纹,他的眼泪。
你能写下的文字,都是你的血。
或许,是闰土脸上的皱纹和眼泪,让你把更犀利的文字,刻满那时,还很黑暗的天空。
与椅子的作战
你身上,越来越低的温度,在暗夜里被陪你坐着的,一把椅子,吸收。
很长的日月里,你用一身瘦硬的骨骼,加上瘦硬的文字,坐烂了一把竹子做的椅子。
淹没在竹子,死后的声音里,你不想让世界听见,你也会陪着,你的文字哭泣。
你也不想,一身孤独地,坐在这些死寂的夜里,只用愤怒的文字,为吃人者挖掘坟墓。
你想挣脱,一把椅子的束缚。你想迈开,走上街头的步伐。你想挤进,你的学生的队列。
你在挣脱之前,想一炬焚烧,堆在书桌上,这座山一样的手稿。
连同这把,坐烂的椅子。
穿过你,用文字,点燃在暗夜里的那些火光,多年以后,我看见你,还坐在你的椅子上。
在许广平的心里
只要这世上有你,她就带着,一脸安心的微笑坐着。
因为太阳,会照在她的身上。
很多时候,她会寄上一个细心的抚摸,让它落在,你被这些浸满苦味的文字,彻夜折磨得,消瘦下去的身上。而更多的抚摸,落在带着你体温的茶杯、稿纸和笔墨上。
天亮了,她还用抚摸,整理被你在书桌上挥洒过的,又一个凌乱的夜晚。
在她眼里,你吸烟也好,讲课也好,或就只是一手叉腰,一个人站在夜晚的尽头,远远地微笑,也是她看得心疼的,人间风景。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能完整地活着?
只要这世上有你,有你的声音,就有声音里的太阳。
穿过暗夜,照在她的身上。
你像又瘦了一圈
你瘦了一圈。因为一个青年,在长夜里,流完最后一滴血。
野草,收留了他的血的干净。野草,在大地上疯狂地生长。
你却收留了他的血的痛苦,血的狂怒,让你又瘦了一圈。
独坐在长夜里,你这是送行。笔墨尽头,血在疼痛地绽放。
很多文字涌来,你这是诅咒。让屠杀者,也饮下血的铅弹。
你像又瘦了一圈。那些流痛,你的血,也让中国瘦了一圈。
你不忘对奴性下刀
你知道,奴才做了主人,也不会废去“老爷”的称呼。
尽管这称呼,让他们活得,没有一点人的样子。
也没有从丹田里,呼出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气息。猥琐的声音,碰不响缺钙的骨头,也碰不碎漆黑在心里的,一抹夜色。
你想剥皮一样,剥掉他们身上的奴性。
你犀利的文字,就是你唯一的手术刀。
你也知道,一个人身上的奴性,不是剥掉一张皮,那么简单。奴才做了主人,奴性的基因,也会裂变。
这样的裂变,其实很可怕。
因此,你不忘对奴性下刀。
你没法跟屠夫说话
昏昏欲睡。在那样的暗夜里,没有几个人,会看得清屠夫。
屠夫举刀,正在寻找,那些在很多年轻人血管里,流得很热的血。饮血,在屠夫心中,是一种滋事和享乐。血在刀刃,早已滴得,失去血的疼痛。
你没法跟屠夫说话。
因为空气里,弥漫着血腥,也弥漫着悲伤。
只要屠夫,张开那张口,就是不说一句话,周围空气,也都会被血腥污染。
这让你恶心至极。
甚至因此,像在暗夜里,吃了一只苍蝇。
他们大多没有坟墓
不常落雪的南方,在你伤痛的心里,一天落着,一场大雪。
沿着你,埋有反骨的眉棱,大雪,把山河也背负不起的伤逝,轻轻放在你瘦小的身上。
坐在大雪落下的寂静里,你看见一些死去的青年,从冰冷的坟墓中,带着魂灵走出来,拥挤在你滴血的文字里。他们大多没有坟墓。一场落在,你心里的大雪,就是他们身后,能得到的安慰。抚摸着心里,堆积得透不过气的爱恨,你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伤痕累累的身体。
你想解开落雪的衣襟,还给他们,一块墓地。
多年以后,我从你脸上,还能看见:
他们带着铁镣,在雪地里移动的样子。
一把燃烧的椅子
你用瘦弱的身体,点燃一把,你以为坐满了罪恶的椅子。
为了坐上,这样的椅子,多少青年身上的鲜血,还有在暗夜里,流成河的眼泪,都被无辜地拿去,清洗他们的马靴。你也因此,想从自己坐着的椅子上,挣扎起来。
在你的眼里,椅子是你一生,要用文字的火,烧掉的东西。
尽管你的那些呐喊,都是一把椅子,载着暗夜,载着暗夜里身上还有一些余温的你,从漆黑的笔墨里,血一样磨出来。而更多的人,坐在椅子上,践踏着椅子,周围的世界。
你仿佛看见了,一把椅子,被烧成了灰烬。
你也仿佛听见了,自己加重的,喘息。
你给世界留下一把骨头
你的心脏,带着暗夜里的中国,走向失去你的时刻。
风不动摇,夜色也不动摇。只有你的心脏,在你瘦弱的身体里,带着你的意识,在剩余的文字里动摇。
这个时候,你对一位女人的感激,对一位女人的思念,对一位女人的抱歉,让你冷静了一生的脸上,最后,有些暖色。
这个时候,你还想用尽,眼睛里的余光,去寻找暗夜里的孩子。你还想用千万个爱,唤醒他们。
从你瘦弱的肖像上,多年以后,我懂得你的身体,就是你一生的燃料。
那个时候,躺在椅子上,微笑着的你,只剩下一把骨头。
你给世界,留下一把骨头。
一把很瘦,也很硬的骨头。
# 一次致敬式的写作
耿 翔
我在马坊的一个山村里长大。那时,我们很难读到一些书,但能读到鲁迅。现在想起来,那些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根本与鲁迅和鲁迅的书无关,就像在一个集体里,做着一种无意识的游戏罢了。倒是鲁迅那些线条硬朗的肖像,让一个山村男孩,开始懂得崇拜什么样的男人了。
我们并不懂得鲁迅,但我们热爱鲁迅。
这就是那个时代,塑造出来的我们。至今藏在我的书柜里的,有一本《阿Q正传》,定价三角一分。这就是说,我曾经用不到半元钱的代价读过鲁迅。现在翻看,我当时读书的认真程度,还是对得住鲁迅先生的。我几乎在书的每一页上,都划出不少的虚线、圆圈、三角等符号,表明我对这些文字的态度,也被那些发黄的旧纸张,作为热爱鲁迅的确凿的证据,原样地保留在书里了。
读书的力量,在于观己。我不知道我在鲁迅的文字里,到底观看到了自己的什么。但我一直畏惧他的文字,畏惧他文字里的目光,畏惧他文字里的叹息,畏惧他文字里的冷暖,也畏惧他文字里的结局。那是很多事件的结局,也是很多人物的结局。那些结局,也就是鲁迅给一个愚昧年代的结局。我更惧怕的是,没有活过他的文字的鲁迅,那么早地走了,那些被他痛打和同情过的人和事,却在我们这个没有他的年代,又活了过来。我们的身边,有阿Q,有闰土,有祥林嫂,他们活在我们的意识里,也活在我们的行为里,他们是我们很难改变的DNA。
没有了鲁迅的目光,很多事物,我们还看不清楚。
鲁迅说过,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鲁迅走了,留下这么多不朽的文字,我们这些必朽之人,能在他的文字里,呼吸上几口他的灵魂里的气息,也就算被鲁迅熏陶、滋养、教诲过,也不枉是一个读过一些书的人。因此,我不敢过多地思想鲁迅。为了给自己下台阶,就借用别人的说法,称自己时不时进入到鲁迅的文字里,是一个人在那里私想鲁迅。
直到有一天,读了无场次非历史剧《大先生》,我才发现,那是李静的一次文字探险。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因此,只要读过鲁迅的人,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同程度地有一个不一样的鲁迅。我从李静的鲁迅中,读到了鲁迅的泪水,读到了鲁迅的血液,读到了鲁迅的骨头,也读到了鲁迅的笑。这些,无论在李静的心里,还是与我以前读过的鲁迅,都是很不一样的。
我也发现,时至今日,鲁迅就连身体,也没有离开我们。
他还坐在那把椅子里。他手上的烟头,还没有掐灭。
我还发现,从鲁瑞、朱安、许广平这三个与鲁迅生死相连,又命运不同的女人那里,去大胆地读一读鲁迅,或许因他的文字的不朽,而对很多人显得遥远、肃穆的鲁迅,距离更近一些,形象也和蔼一些。
我也就放下畏惧,写了《坐在椅子上的鲁迅》。
我最想说给鲁迅的一句话:“你的文字是一副中药。”
从最初懵懂地读鲁迅,到第一次写鲁迅,其间的时间跨度接近五十年。
有关鲁迅,就是看见了一朵朝花,也只能夕拾。
# “仿古”的象征主义:鲁迅与21世纪新历史书写
王年军
诗人耿翔的这组《坐在椅子上的鲁迅》,以鲁迅生平作为依据,以《野草》作为基本范例,用当代人的视角重构了鲁迅的生活、思想和诗文创作。它也内涵了21世纪诗歌、小说甚至视觉艺术领域创作中的一个基本倾向,即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再现之间刻意制造的陌生感、不匹配感或间离感,历史仍然在那里,但是,它只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环境,作为一种史实,而情感逻辑则被抽空。传统的“写实主义原则”强调人物的所思所想受限于环境,这是雨果、福楼拜的历史小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或钱穆的《孔子》共有的一种历史限定。但是,21世纪的虚构写作,在书写历史时,不再受困于客观环境对人物的限定,这是一种此前少有的想象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比如关于柳如是、鱼玄机的想象和写作,对于屈原、陶渊明、谢安、《红楼梦》人物的想象和写作,很多时候是以把他们作为“现代人”来理解的,也对戏仿、反写、逆写、“戏说”抱着相对开放的态度。李静的《大先生》我没有看过,想必也是这样一种书写/演绎方式。这种想法受到我最近看过的电影《燃烧女子的画像》和《兹山鱼谱》的启发。《燃烧女子的画像》通篇采取了新古典主义的视觉风格,也是法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流派。相对于古典主义,它简化了背景,突出人物,强调理性控制下的几何构图和比例分配,追求色彩的鲜明和单纯。这种没有光源依据的、非电影、反电影的光学原则,当然不会反“现实主义”——窗口显然更亮,但是,不会因为窗口而呈现光源、光斑、光的对立的阴影。同样,《兹山鱼谱》则以东亚特有的古典山水画的构图来呈现故事发生的“前现代”空间,作为传统士大夫被贬谪后精神情境的直接“表象”形式。这种书写,有时实际上是一种“解读”,就像说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第一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伴侣”,同样是言之成理的解读,不过,这种解读也不时表现出人物跟时代的格格不入和相互抗拒,因为,那些历史人物往往深深地内在于自身历史的情感结构之中。
同样,对鲁迅的书写也是如此。这一组作品在形式上是对于鲁迅的经典名作《野草》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偶尔的一两篇仿作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系统性地对《野草》进行回应。诗人耿翔的这组《坐在椅子上的鲁迅》用极有耐心、极为专注的方式,对鲁迅的《野草》的风格、基本意象、散文诗的形式等,进行了一次全面地回返。当然,作者也意识到了,回返历史并不是要“重现”历史,因为,对于历史是什么,后来者置身在当时的“情感结构”之外,永远也说不清楚。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尝试复现那个时代的主导性的文字媒介和技术形式。在组章中,我们发现作者用当代的关切方式对鲁迅的一些关键意象进行重写,重构或“复现”了鲁迅作品的“版画”效果,对比分明、色调凝重、构图沉潜,这种使用文字的方式首先就使读者更加接近鲁迅文字的原初状态。就像作者自陈的:“现在想起来,那些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根本与鲁迅和鲁迅的书无关,就像在一个集体里,做着一种无意识的游戏罢了。倒是鲁迅那些线条硬朗的肖像,让一个山村男孩,开始懂得崇拜什么样的男人了。”也许这组散文诗里版画效果的形成,和鲁迅在作者童年时期记忆中的视觉造型之间,确实有一种无意识的关系。比如,在这组散文诗中,诗人也使用了中药(中医)、血、坟墓等色调黯淡的意象。诗人写道:“你以为人间的伤逝,会让所有死去的文字,不再腐朽下去。因为你见过的血迹太多。多到泪水,不能擦拭。”这种句法,首先就为读者唤起了阅读鲁迅的场景,建构了情感上取得认可的前提。
当然,任何重写也都是在新的语境下的改写。鲁迅在中国诗歌史中的地位,正在经历重新发现的过程。一般会认为,鲁迅只写过像《我的失恋》这样的“打油诗”,或者说就是旧体诗,像《自题小像》《惯于长夜过春时》这样的经典作品,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野草》是散文诗,当然也受到了关注,而且比重相当大,像日本学者竹内好等对其的评价就非常高。但是,《野草》在诗歌史中,在“新诗”中的位置,一向是比较暧昧的,因为,新诗史很少把鲁迅的《野草》视为诗人的作品,他的小说家的地位遮蔽了他作为诗人的贡献。如果《野草》是一个只写过诗的诗人的作品,可以想见,它在诗歌史中得到的研究至少会比现在充分。《野草》创作时间不可谓不早,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相比郭沫若的《女神》、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野草》相对来说确实晚几年。但是,像张枣这样在20世纪诗歌史上卓有成效的后起之秀,对《野草》也是赞赏有加。作为在探索诗歌语言方面颇有建树和心得的诗人,他就认为鲁迅才是中国诗歌史最不可忽略的开创者。废名有一句话,说要区分用诗的形式写成的散文和用散文的形式写成的诗。他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新诗应该走的途径。这呼应了作者创作观中的话:“在我的文学体验里,自从有了散文诗的概念,就以为《诗经》是散文诗,汉赋是散文诗,宋词是散文诗,元曲更是散文诗。”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的《尝试集》只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散文,它是分行的,遵从了抒情诗最基本的要求准则,但鲁迅的《野草》这样的“散文”,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的诗。它是不分行的,但是,它的语言的密度、思想的强度,以及思考问题的充分“现代性”的感觉,使它不同于一般性的散文而接近于诗。
张枣延续了朱自清首次提出的中国新诗中自由诗、格律诗和象征诗的三分法,而对鲁迅的象征诗情有独钟。他曾经对胡适开创的自由诗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在评论中直言:“然而,作为白话诗的始作俑者,胡适还不能说是开启了新传统。问题主要在于,他不能从隐喻和象征层面区分语言和日常语言,辨别平淡与诗意。由于将现代的诗歌语言精简成了文字改革的工具,胡适取自庞德意象主义的‘文学八事’流于肤浅。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反诗的举措能够把握新语言的实质。胡适对新主题的处理,如同他在《尝试集》中写的诗,实际上漏掉了他那个时代真正的脉搏。”这段话出自刘金华根据张枣的英文论文翻译的《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载于《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之后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在张枣看来,与胡适开创的自由诗路径相对照的是象征诗,代表人物包括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及其追随者们,但是,在这些人中,张枣又认为只有李金发和鲁迅获得了最高的成就,“就现代世界真实的主观感受而言,两位诗人可谓独一无二,前所未有,他们惊人坦率地承认,生命是一种诅咒,一个陷阱,在其中个体会持续地感到绝望与不满。”这里,张枣明确指出,现代诗之所以“现代”,不是因为采取了自由体、散文诗的形式,也不是因为采取了欧化的格律和新的节拍,而是诗中抒情主人公的现代意识。“鲁迅是真的现代,这不仅在于他文章中前所未有的尖锐语调与文辞,还在于生存困境已成为他首要的主题,压倒性的虚无主义成为《野草》独有的象征。”张枣指出,鲁迅对“生存困境”的突出关注,以及《野草》中的“虚无主义”,才是他成为独一无二的现代诗人的关键。并且,他根据自己一以贯之的语言诗学的观念,指出鲁迅“将生命危机等同于语言危机”,因此,将生活的绝望和语言的绝境联系起来。
很难说,对鲁迅散文诗的诗歌史关注是因张枣而起,但确实从他开始,对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增多了。在《坐在椅子上的鲁迅》这组诗中,诗人有意地回到了一种“古旧”的象征主义文学模式,它曾是鲁迅、李金发、卞之琳等那一代诗人的基本的情感结构,决定了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想象和认知。这种技术上的造旧和仿古使《坐在椅子上的鲁迅》这组诗有一种特殊的阅读感觉,就像来自一个百年前的文学家的作品。但想要重写鲁迅是很难的。它是一个比如向杜甫致敬一样,一般作者不敢轻易触碰的主题。当然,作者本人说得很好,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鲁迅说过,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鲁迅走了,留下这么多不朽的文字,我们这些必朽之人,能在他的文字里,呼吸上几口他的灵魂里的气息,也就算被鲁迅熏陶、滋养、教诲过,也不枉是一个读过一些书的人。因此,我不敢过多地思想鲁迅。为了给自己下台阶,就借用别人的说法,称自己时不时进入到鲁迅的文字里,是一个人在那里私想鲁迅。”(引自《一次致敬式的写作》)诗人耿翔在这里重构了鲁迅的一些面貌,他认为是“私人构想”的鲁迅的面貌,这为他对鲁迅的解读和再创造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比如他写朱安,就用一种现代的、当代的意境,告别了五四启蒙话语的表达方式,来理解鲁迅和他母亲逼迫他娶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对此进行了一种当代的、解构的想象,其中很多画面,都是从鲁迅从未关注的视角投递出去的目光才能看见的。“为了弥补自己,没有放脚的过错,朱安给粽子似的小脚,穿上好大的绣花鞋。”这句诗里,饱含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弱女子的无奈。
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地通过作者对于朱安的想象而批评鲁迅,而是意识到了鲁迅式的困境,是五四那一代思想家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到了当代,我们这些被新文化所哺育的人,却可以有更多的余裕,去看待自己跟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对朱安形象的重写,也意味着对看不见的“旧人”的重写。在库切重写《鲁宾逊漂流记》的《福》中,把小说的主角变成“星期五”,设想他是一个被割掉舌头的人。后现代元小说的特征,就是去“逆写”经典小说中的人物,把作为背景的次要人物作为主角,而主角“光环”的合理性则被质疑。朱安形象的变化,也折射了近一百年中国的革命、战乱、建设、发展中对待传统、对待新文化的态度的多重转折和重写。她和闰土不一样,在阶层位置上,朱安和闰土一样,都是历史上“消声的人”,但鲁迅对闰土有同情,而朱安只获得了鲁迅的冷遇。“她早想以一位女人的,清净之身,为你死去。/如果问罪于你的世界,真的需要,一个祭品。/只是心里的,冷,让她走不到,鬼魂那里去。/朱安,很像一个渐冻人,她没有力气,为你赴死。”诗人采用了与第二人称的“你”对话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封建”女性在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中的失语。朱安就像中国旧文化的肉身,作为一个幽灵放在鲁迅身边。要葬埋旧文化,就要葬埋这个活生生的人,但是,出于人道主义又不能真的“葬埋”活着的生命,鲁迅只是搁置了对她的关注,任她在历史的残酷发展中自己湮灭。这让我想起《战争与和平》中同样有一个被历史湮灭的善良的灵魂,她就是罗斯托夫家的养女宋妮雅,她对尼古拉怀着不可磨灭的依恋和挚爱,这种情感并不比任何最崇高的情感卑微,但她却因为缺乏嫁妆而最终开成了一朵“谎花”,成为除诡计多端的布莉恩小姐之外的另外一位始终孤独的女性。这是历史逻辑的残忍与非人。诗人耿翔有意识地对这个幽灵般的角色给予了一些关注,它告诉我们,任何幽灵都是飘荡在真实的空间中的。幽灵是幽灵,意味着它是无法被放逐的,它是心事重重、挥之不去的,总是会回到人间,回到大街上,以它的还魂和重现,呈现出历史被遮蔽的部分,表达歧路丛生的历史的复数可能。幽灵往往是单一线性叙事逻辑容纳不了的赘余物,是没有得到合理葬埋的生命,怀着怨愤、凄凉的感觉重新回到人们已经忘却他们的生活。因此,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幽灵,曾经在五四一代离家出走的人之中被葬埋了,一个“反面的娜拉”——没有离家出走,也没有出走的能力,没有觉悟,没有获得“启蒙”的光照,一个“旧女性”,锁闭在自己的铁屋子中,鲁迅甚至不愿意叫醒她,怕她忍受不了清醒之后的痛苦。而时过一个世纪之后,她又在后来者诗人的笔下重返人间,获得自己的一点点对生活的基本感觉。朱安的被发现意味着我们已经从革命的逻辑进入后革命的逻辑,从启蒙的逻辑走向启蒙辩证法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需要为此而受到后革命的审判。鲁迅仍然是一个真诚、宽容、有同情心的鲁迅,朱安也是一个被历史残酷地卷入其中、而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与关注的朱安。
选自《散文诗》2022年第2期
编辑:王傲霏,二审:牛莉,终审:金石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