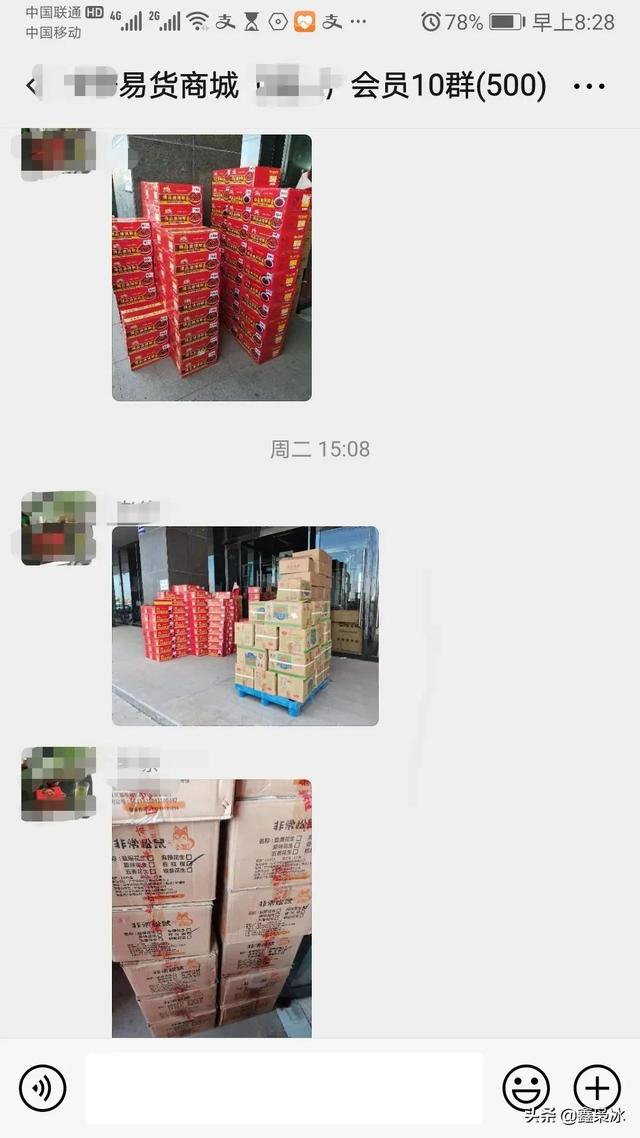FANGDONG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的疫情,这些事情使得民众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逐渐意识到稳定第一。所以,网络上出现了一句调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跟豆瓣上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一样,甫一成立,应者云集,成员迅速从个位数增长到了8万人。
不同的是,“985废物引进计划”以 “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作为符号和标签定义自身,现实生活中谁也不认识谁的“小镇做题家”们,在这里找到了同伴,互相抚慰。
而民众的共鸣,则是就业和生活越来越艰难,他们求稳,想安全地生活下去。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明星考编,加之某新闻媒体带着嘲讽口吻说的那句“小镇做题家”的推波助澜,引爆了舆论。
这几天,就此事我问过至少10个在校的以及已毕业的知名高校生,他们给出的答案神奇一致:他们并不是在质疑明星考编,只是想知道考试和录取流程是否透明公正,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至于“小镇做题家”,上海同济大学的晢西说,“‘小镇做题家’是一种兼具优越感和无奈感的自我认知,这个称号只可用来自嘲而不可以被嘲讽。某些人让其变成嘲讽,可恨可恶。”
FANGDONG | 房东俱乐会
撰文:黑泥 美编:小樱 校对:大豆
01
小城镇青年被剥夺了什么?
“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背后所涉及的是教育公平、阶层流动、就业苦难等问题。
小镇青年,十年寒窗,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进阶,到了大学校园后,突然发现曾经的优越感不在了,他们好像跟别的同学出现了差距。
初高中时,他们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到了大学,他们的面前仿佛出现了千万条路。
他们还需要摸索。这个过程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深有体味。
“我们班级举行《菊与刀》的读书会,是介绍日本文化的,读书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讨论其它国家文化,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班里近1/3的同学都有出国经历;读大一时,有一门计算机编程课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基础,而我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一直搞不懂,最终通过补考才过;除此之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及特长方面,跟同学们差距也很大。”
在上海同济大学读大二的晢西,老家是豫西南的一个农村。她在读大学之前,没有出过省,最远只是去过省会郑州。
晢西读的是理工科,虽然她是00后,但是在2020年疫情上网课之前,她接触不到智能手机和电脑,“因为家里根本没有。”
晢西感慨说,作为生在河南农村的学子,要想走出去,通过应试算是最容易的一条途径,而这种应试大概率会让你成为一个除了学习成绩还可以,其他样样都不行的人,这种人在大学多元的评价体系中是很难脱颖而出的。
晢西看到了学习,而读华南师范大学的妮妮感悟到的是生活。
“读大学的这两年,我明显的感受是,一线城市的人都更加放松地生活,会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让我明白奢侈品不是一个人自信的来源和底气。”
妮妮生活在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属于三四线城市。父母都是生意人,条件不错,是三线城市里的中产家庭。
妮妮姊妹三个,她是老大。据妮妮的母亲讲,从小到大,妮妮从来没有让她操心过,一直都是以学霸的形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非常省事。
由于家庭条件相对优渥,在三四线小城生活的妮妮的认知中,奢侈品会是一个人的底气。而当她接触到大城市人的一面后,她觉悟到,也许精神追求才更高级,外在的附着远没有从内向外散发的自信更重要。
武汉理工大学的呦呦并不认为这就是他们放松的生活,只是周末、节假日犒劳自己的一种方式。她觉得,“类似于聚餐、看电影、旅游之类的,在我们农村基本享受不到,那些城市人只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是的。布迪厄说,“资本是劳动的累积”,尤其是文化资本,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需要长时间的体悟和内化。
从读大学的那一刻起,他们身上注定摆脱不了原生家庭带来的烙印,但不是不可以改变。
对大城市的一些学生来讲,大学可能是一段日常生活的延续;而对于小城镇学生来讲,大学就是一段新生。
小城镇出来的学生,需要对这个社会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认知,要吸收更多的东西来弥补之前因为信息差导致的不平等。
就好像同济大学晢西接触了那么多优秀的同学后发出的疑问,“他们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那么多的优质资源,高考成绩不应该更好吗?录取分数为什么比我们还低?”
我无言以对。三十年前,“小镇做题家”也许还值得自豪,可以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可现在呢?却公然被江西那位地主家的傻儿子嘲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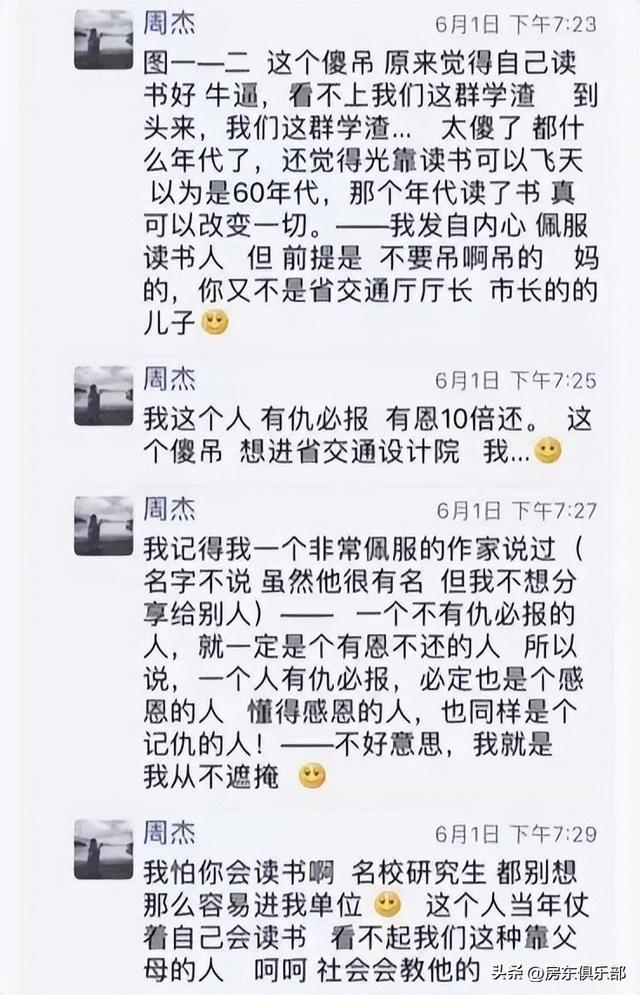
出生决定了的资源,我们无法改变,但通往成功的渠道应该一视同仁。“小镇做题家”,刺痛的不是人心,而是公平正义。
不是吗?
02
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
知乎上就读于清华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的一个博士认为:
至于很多人说,做题家们缺少混社会的能力,到了社会上容易格格不入。我觉得其实也并不需要过于担心,因为那些所谓的社会关系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
当你具有了价值后,自然会赢得善意和尊重,毕竟他们每次嘲讽的对象,都是那些竞争失败的做题家。而那些成功了的,反而会被他们逐出做题家的行列。当今社会上很多失败的中年人,其实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小镇做题家”。
比如从北京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到落魄贫苦户的伍继红,因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和为人处世的能力,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还有高分低能啃老18年的张进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这种上一代极少数的“小镇做题家”,也许太在意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了吧!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有学生问网红考研老师张雪峰怎么看待“小镇做题家”?
张雪峰说,“我就是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你不要特别在意自己的一个出身,出身并不影响你将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不是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贬低我们的人,人活着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自己。除了你自己可以说放弃,任何人没有资格。”
张雪峰以前在一个视频中讲,他从没有想到能从齐齐哈尔的一个小县城到郑州大学读书,也从没有想到能在北京买房娶妻生子,更没有想到还能成为网红培训老师,最后居然还拍了部电影。
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2018年张雪峰在西班牙看球赛时,在梅西拿到奖杯之前,他已经跟那个奖杯合过影了。他一脸骄傲地说,“梅西亲吻的那个奖杯,上面是有我的口水的。”
人不是看你在什么地方,而是看你往什么地方走。
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小镇做题家”都有着自己清晰的判断,他们不仅读书多,也明白怎么跟“双水村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上海同济大学的晢西说,她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对跟大城市同学之间的差距做了设想,但是当这种差距真实地摆到面前时,还是有很大的落差感。
她能坦然接受这种差距,“是因为我的祖辈父辈们的财富积累还不够。”
对于未来的计划,大的方面,她会认真对待学业,在这个前提下,学业之外,“借助学校的平台,借助上海的资源,不断锻炼自己,争取缩小这种差距。”
妮妮的打算是,“更加努力,考研或者留在广州发展。”
呦呦的想法很纯粹,既然起跑线不一样,那就更能激励自己,“努力争取更好的,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发挥自己所长,认真干就好。”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大,各行各业又不景气,毕业人数反而逐年增加,促使考研、考编变成热潮,以至于很多人觉得,“编制真香”,认为到了宇宙的尽头。
而受访的这几位年轻学子,他们的共同点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觉得宇宙的尽头并不一定就是编制。
时代的卷子出来了,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努力不止。
这个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