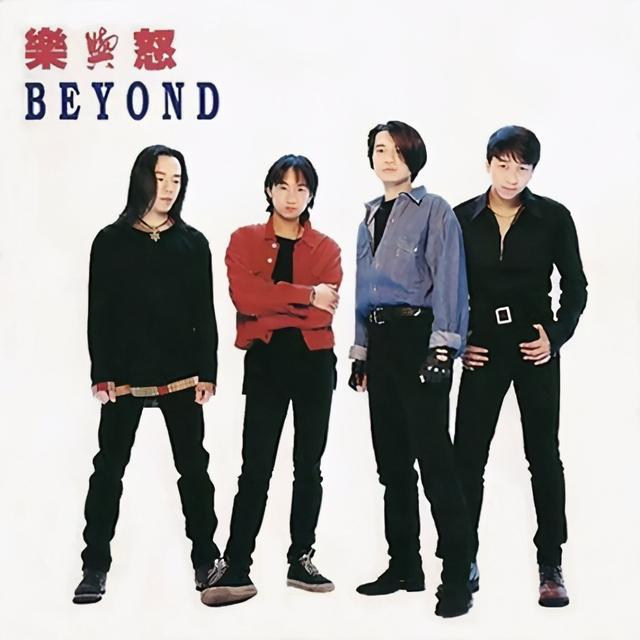拜会亚鲁王
——《非遗中国行》国家级民间文学非遗项目《亚鲁王》史诗导演手记
韩胜勋
我此去贵州是为了完成央视《非遗中国行》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亚鲁王》的拍摄,飞机飞到贵州的省界,从弦窗望下去,千山万壑,层层叠翠,让我的心情飞腾起来,我在想:这千山万岭曾是亚鲁王的“王土”,可哪一座山峰是他当年栖息之地?哪一条河流该是他的饮马之川?是的,自从接到这个任务起,那个2500年前的亚鲁王就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我开始畅想他的形象,上网搜索关于他的内容,他好像就是远处的一座山峰,而我,不管有多么遥远,也要走近他、拜会他、领略他的神韵。

韩胜勋老师和亚鲁王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江在中兴合影 (摄影:杨正超)
亚鲁王研究中心在穿上洞唱诵《亚鲁王》祈福歌
燕子洞里的暗河与格凸河相通,洞里高大幽深,碧波荡漾,我们接下来的唱诵从洞里开始。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的杨正兴 、杨正超两人身穿苗族长衫,手持宝剑站在船头,唱诵史诗中《万物祖先同源》的片段。史诗以朴实的语言告诉大家,世界上的万物都是有灵魂的,他们都是共同的祖先演化的。这和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说“天地同根,万物同源”如出一辙。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亚鲁王就有了敬畏自然的思想,就有了天下人是一家的观念,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老子誉满天下,而亚鲁王还有许多人并不知晓,我们觉得作为一名非遗文化的电视工作者,更有责任把国家级文化遗产——亚鲁王介绍给大众。
随行的东郎告诉我,亚鲁王正是自己理念的践行者,史诗中记述了亚鲁王率部迁徙的经历:当家族里刀兵相见时,他为避免厮杀,躲避战争,宁可带着族人长途迁徙,退避到难以生存的贵州山地,刀耕火种,重新开始生活。杨正兴 、杨正超的唱诵显示了苗族人歌唱的天赋,收放得当,意境空灵,山洞的回声更增添了神秘之感,仿佛那是从遥远年代传来的真经。在悠扬的唱诵中小船驶出燕子洞,连绵青山迎面而来,无论是目光还是心灵之光都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我们决定让好戏连台。接着由东郎王凤书老人登上船头唱诵史诗中关于《乐器》的片段,歌中唱道:一个人死去了,可是她的灵魂却说:没有唢呐,我不会走,没有鼓声,我不会走。尽管我已经知道所唱诵的内容,但老人富有激情的唱诵仍使我的心灵震撼。是的,即使死了,灵魂也离不开唢呐声,离不开鼓声,那是对于音乐多么的挚爱!——顿时我找到了苗族人视音乐为生命的文化根源,也理解了苗族人为什么有那么丰富多彩的歌舞,《亚鲁王史诗》不愧为认识苗族文化的一把钥匙。岸上青山移过,船下碧水横流,远处不时传来苗族姑娘欢快的歌声,我想:历史就像这一条河由遥远而来,向着遥远而去,但是在这恒久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民族的人文精神。《亚鲁王史诗》2500年来,其神其韵就像这格凸河上永远绽放的浪花,一直盛开着无尽的美丽。
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的杨松、杨小冬唱诵了关于《盐》的片段,其中唱道:“在青树下∕在青树脚∕你会看到井里的蒜颗像黑色的牛眼珠∕你会看到井里的盐颗像紫色的羊眼珠”。从史诗中描绘的“黑色”和“紫色”来看,那时制作的不是海盐,不是池盐,也不是井盐,而是岩盐。使我们知道2500年前,苗族人已经有了制作岩盐的技术。由于苗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这样的资料在别处也无处可寻,正是《亚鲁王史诗》填补了苗族古代历史的空白。我之所以选取这一个片段,就是为了证实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事实上《亚鲁王史诗》是一个浩海,它包含了苗族的创世史、征战史和迁徙史,具有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宝贵价值。对于苗族人来说,它就像史诗中唱诵的盐一样不可或缺,有了它,苗族的生活才更有味道,苗族人民才更有精神。
此行我们还有一个计划,那就是聚焦亚鲁王文化传承人,看一看目前亚鲁王文化传承的现状,首先采访了《亚鲁王史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兴华。他1945年出生,银发长须,透着学者的气韵。回首文革黑白颠倒的日子,他说,当时把《亚鲁王史诗》当做封建迷信,把东郎当做迷信的传播者,自己随时都会被列入“牛鬼蛇神”之列。那时陈兴华在紫云县粮食局工作,冒着入狱丢饭碗的巨大风险,在暗地里坚持做东郎,2012年成为《亚鲁王史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接到证书的那一刻,他热泪长流,发誓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亚鲁王文化的传播事业。陈兴华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做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传承基地,坚持免费教学。历史以来学习唱诵《亚鲁王史诗》有许多禁忌,每年只有正月和七月才可以进行,像无形的绳子束缚了史诗的学习和传播;他率先打破千年的陈规,要求弟子“只要内心虔诚,随时随地都可以学”。陈兴华还第一个把由他传承的陈氏分支《亚鲁王史诗》版本,整理成册,由口头流传转变成文字流传,并且修改了必须是当面亲授的学规,使便捷的听录音学习成为一种崭新的学习方式。
杨正江和他的团队也是我们采访的重点。杨正江多年来投身亚鲁王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荣誉称号,目前担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兼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说,刚开始时最大的痛苦就是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像孤雁挣扎在探寻亚鲁王文化的的路上。我们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应有的宽容,把《亚鲁王史诗》当成封建迷信,以致这种错误的认识成为了许多人的认知,家人和朋友责怪他们:社会上有那么多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非要干封建迷信的事?许多东郎也心有余悸,怕引火烧身,不敢配合他们的工作。杨正江不懈怠,不气馁,带领团队坚定地向前走。他们参与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史诗》挖掘与出版项目,成为2009年度中国重大文化发现之一;他们完成了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境内1778名东郎的普查登记与档案建立;举办了万人祭祀亚鲁王的大型活动,举办了紫云县第一届“千名东郎唱诵史诗大赛”。让《亚鲁王史诗》在紫云地区以及社会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传播。
说到此你也许会问:你文章的题目是“拜会亚鲁王”,采访这些人和“拜会亚鲁王”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我们常说: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家长的影子,那么我们从亚鲁王的子孙身上,不正是可以看到苗族祖先亚鲁王的影子吗?是的,无论是陈兴华,还是杨正兴和他的团队,他们作为亚鲁王的后人,身上的那份执着,那份坚强,应该有亚鲁王流传下来的基因。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亚鲁王文化鲜活起来。
当然你也许会说:亚鲁王是2500年前的人物,拜会他犹如拜会天上的星星,——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我只能怪你书生气了,我们的贵州之行,从壮美的山水中感受到亚鲁王其形,从史诗唱诵中感受到亚鲁王其心,从亚鲁王子孙的身上感受到亚鲁王其神,可以说处处见到了亚鲁王的影子,能说没有拜会亚鲁王吗?
来源:亚鲁王公众号 韩胜勋 亚鲁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