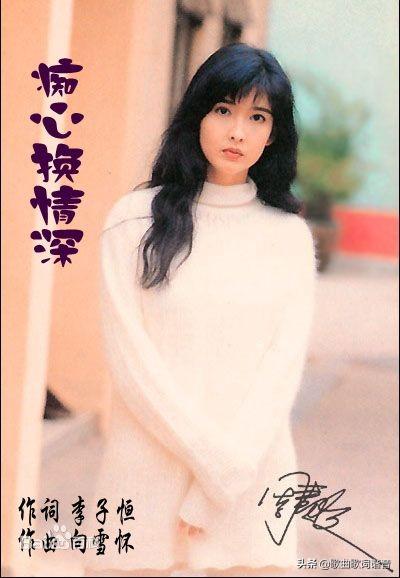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回目解释:①“秋爽斋”,探春在大观园的住处。
②海棠社:由探春倡议成立,因第一次集会所作之诗为“咏白海棠”,故名“海棠诗社”。诗社成员有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及李纨。李纨为社长,迎春、惜春为副社长。
③“蘅芜院”,宝钗在大观园的住处。
重点情节:①“海棠诗社”的成立。 ②宝玉和众姐妹的诗号。 ③宝钗、黛玉《咏白海棠》诗解读。 ④李纨评诗。 ⑤宝钗论诗。
经典语言及解说:1、“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
这是黛玉打趣探春的话。探春住在“秋爽斋”,院子里种有梧桐芭蕉,她对芭蕉情有独钟,说“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于是“蕉下客”就成了是探春在海棠诗社的别号。
黛玉听了后,马上联想到“蕉叶覆鹿”的典故来:春秋时,郑国樵夫打死一只鹿,怕被别人看见,就把它藏在坑中,盖上蕉叶,后来他去取鹿时,忘了所藏的地方,就以为是一场梦。黛玉信手拈来,“使巧话”戏谑探春是一只小鹿,还要做了鹿肉干来。一方面说明黛玉博览群书,见多识广,聪明而富有才气;另一方面又表现她爱说爱笑、活泼可爱的调皮性格,——谁说黛玉只爱哭呢!
2、“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
这是探春“反击”黛玉的话。“娥皇、女英”,传说是尧帝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帝。“湘妃竹”又名斑竹,相传舜帝南巡苍梧而死,娥皇、女英在江湘之间哭泣,眼泪洒在竹子上,从此竹子上就有了斑点。黛玉住在潇湘馆,潇湘馆多竹子,“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有千百竿翠竹遮映”。黛玉又爱哭,前八十回里就写到有十五六次。
探春称黛玉是“潇湘妃子”,既合乎潇湘馆的情景,又与黛玉的性格相吻合,的确是个“极当的美号”,庚辰本夹批道:“妙极趣极!……因一谑便勾出一美号来,何等妙文哉!”从此这一独具诗意的别号,就成为林黛玉的代名词。
3、“我送你个号吧。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
这是宝钗说的话。宝钗给宝玉起别号,先说他是“无事忙”,后说他是“富贵闲人”。两个号似乎都含有讥讽之意。
“无事忙”,指忙于正务以外的事。在宝钗看来,读书做官才是正务。而宝玉却是“愚顽怕读文章”,不愿谈仕途经济,骂读书人是“禄蠹”,讨厌和贾雨村这样的官场上的人打交道。他整天只喜欢钻在女儿堆里厮混,如关心在地上划蔷的龄官淋了雨没有,带着茗烟到处去寻找茗玉小姐的庙,陪着晴雯撕扇子玩,给黛玉讲耗子精偷香芋逗乐,等等。
“富贵闲人”的生活常态是,上有贾母宠溺,周围有群钗簇拥,每天读一点庞杂兼收的书,写几首风花雪月的诗,发几句愤世疾俗的牢骚话。分明就是大观园的“绛洞花王”。
“绛洞花王”一说“绛洞花主”,是宝玉以前用过的旧号:“小时候干过的营生,还提它作什么。”脂砚斋一针见血地指出:“赧言如闻,不知大时又有何营生。”批评宝玉长大后仍然毫无作为。至于宝玉究竟是“花王”还是“花主”,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把大观园当成了他的王国,每天乐在其中,乐不可支。
4、“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这是宝钗说的话。秋爽斋初次结社,李纨提议咏白海棠,迎春提出疑问:“都还未赏,先倒做诗。”宝钗这番话,算是对迎春的回答。
这里宝钗提出了一个观点:诗歌是“寄兴写情”,而不必拘泥于景物本身。所谓“寄兴写情”,就是寄寓个人的思想情趣,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如宝钗的《咏白海棠》,表面上写的是白海棠,实际上写的是她自己。首联“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象征她端庄稳重、矜持谦和的性格。颔联“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表现她不爱艳装、不作浮语的做人原则。颈联“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表现她内敛隐忍、圆融和顺的处世态度。尾联“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寄托她洁身自爱、与世无争的情怀。
宝钗在她的诗歌中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脂砚斋语),果然诗如其人。
5、“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
宝玉让秋纹送鲜花给王夫人,王夫人赏了秋纹两件衣服,秋纹受了太太的恩典,有点得意忘形。晴雯见此说了这番话,一下子得罪了三个人。
首先是秋纹,晴雯看不惯秋纹得意的样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骂她是“没见过世面的小蹄子”,讽刺她做人没有骨气,对主子卑躬屈膝。
其次是袭人,在晴雯眼里,袭人和她一样,是“这屋里的人”,一点也不比她“高贵”,她甚至觉得袭人各方面还不如她,没有她漂亮,没有她能干,没有她伶牙俐齿……她嫉妒王夫人把袭人当作“准姨娘”看,借讽刺秋纹而挖苦袭人。
再次是王夫人,“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就是针对王夫人的。在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夫人根本就不认识晴雯,她凭什么冲撞王夫人呢?别说是丫鬟冲撞主子,就是普通人冲撞普通人,也应该师出有名!
晴雯这样做,并非体现她的反抗精神,一切都是因为心理不平衡。她所追求的,不是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平等,而是奴才与奴才之间的平等。
6、“什么要紧,不过玩意儿。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儿。告诉他,他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
这是袭人说的话,“他”指湘云。诗社成立后,宝玉忽然想到湘云还不知道:“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立马就要派人去接。
袭人对宝玉说的这番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诗社就是个“玩意儿”,供公子小姐们娱乐消遣而已;二是湘云寄养在叔父家,毫无地位和自由,凡事“作不得主”,来去“由不得他”;三是湘云是个急性子,说话直来直去,做事风风火火,诗社这件事只会让她“牵肠挂肚”,备受折磨。
袭人不仅了解湘云的处境和性格,而且与湘云的关系也非常好。十年前,袭人曾服侍过湘云一段时间。后来,湘云回家了,袭人也被老太太派去服侍宝玉,但是两人的感情联络一直没有断。如第三十一回,湘云带了戒指来送给袭人等;第三十二回,袭人请湘云帮忙做针线活;第三十七回,袭人以送水果和糕点为名,借机把湘云喜欢的玛瑙碟子送去,等等。这些事情虽是小事,却能说明她们之间名为主仆、实为姐妹的感情。
袭人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去接湘云,而是暗示宝玉,只有贾母出面派人去接,湘云才不会为难。
7、“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
这是宝钗对湘云说的话。不仅袭人了解湘云在家里的处境,宝钗也了解。湘云每个月的零花钱很少,只有“几串钱”,具体是多少,确切数目不详,但是连自己的“盘缠”都不够,“盘缠”即零用钱。湘云平时还要做针线活,有时要做到三更天(第三十二回)。还要经常被婶娘抱怨。由此可见,湘云的处境非常艰难。
宝钗一方面嗔怪湘云夸下海口要作东,说话缺少思量,做事未能“瞻前顾后”,另一方面又让哥哥薛蟠送来螃蟹、果碟和好酒,真心帮助湘云解决实际问题,避免让湘云尴尬出丑丢面子。
8、“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
这是宝钗对湘云说的话。宝钗怕湘云多心,强调自己出于“一片真心”,丝毫没有“小看”湘云的意思。
宝钗不仅帮助过湘云,而且还帮助过很多人。如第三十二回,她拿出新做的两套衣服,给投井而死的金钏装殓;第四十五回,她给生病的林黛玉送去燕窝;第五十六回,她“小惠全大体”,让利给管理大观园的婆子们;第五十七回,她帮着邢岫烟赎回当掉的棉衣;第六十七回,她把薛蟠带回来的礼物分送众人,连贾环都得到一份,等等。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在她经常做好事。
俗话说,好人难做。宝钗的担心并非多余,读者中的贬薛派就是这样评价宝钗的。无论宝钗帮助了谁,上至小姐下到丫头,他们都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用小恩小惠来笼络和收买人心。好在湘云没有这样想,“凭他怎么糊涂,连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湘云对宝姐姐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9、“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
这是宝钗说的话,表达了她对诗歌写作的一些看法。
关于诗题,宝钗认为题目不能过于新巧。过分地追求新巧,很容易会走进“刁钻古怪”的死胡同。
关于诗韵,宝钗反对使用“极险的韵”。所谓“极险的韵”,就是用生僻艰涩的、一般人不懂的字作为韵脚。
关于立意,宝钗认为立意是诗歌写作的“头一件”,即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立意一定要“清新”。所谓“清新”,就是新颖不俗气。
关于措词,就是指诗歌语言。宝钗认为诗歌既“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熟话”指前人常用的陈腔滥调,那样就没有新意、没有意境。“求生”指寻求生僻晦涩的文字,故弄玄虚,故作惊人之语。好的语言,就是要“不俗”,高雅而不庸俗。
10、“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
这是宝钗对湘云说的话,谈了写诗和做人(女人)的关系。作为女孩子,会不会写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好分内的事,要学会“纺绩针黹”。纺绩,指织布。针黹(zhǐ),指各种针线活儿。本等,本分。即便空闲下来读书,也要读点对女孩子有益的书。言下之意是诗歌对女孩子用处不大,如果移了性情反而有害。
宝钗深受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经常不失时机地对黛玉、湘云等进行说教。
11、“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
这是宝钗对湘云说的话,谈了如何拟菊花诗的题目。宝钗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题目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二是题目“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三是“咏菊”与“赋事”二者之间要有关联。
这里的“实字”“虚字”,与现代汉语中的“实词”“虚词”意思不同,“实字”指名词,而且是有具体形状的名词;“虚字”指名词之外的其它词类,包括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等。在拟就的题目中,“菊”是实字,其它如“忆”“访”“种”“画”“影”“梦”“残”等都是虚字。
“通用门”,有的版本又作“通用关”,是古代分类字书中的一个门类。“虚字就用通用门的”,意思就是此次写作菊花诗,所有“虚字”都要出自“通用门”,否则就是犯规。
什么叫“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什么叫“赋景咏物两关着”?我们就引用下面一段文字作为回答。
“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
12、“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
这是宝钗说的话。宝钗认为,诗不必限韵,限韵会束缚人。“为韵所缚”写出来的诗,会显得小家子气,不可能是好诗好句。写诗本来就是为了“取乐”的,而不是为了刁难人。
宝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湘云、宝玉等人的赞同。湘云说:“这话很是。”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回目解释:①“林潇湘”,林黛玉,诗号“潇湘妃子”。
②“薛蘅芜”,薛宝钗,诗号“蘅芜君”。
③“讽和(hè)”,讽喻唱和。
重点情节:①“魁夺菊花诗”的故事。 ②黛玉《咏菊》《问菊》《菊梦》解读。 ③宝钗《忆菊》《画菊》解读。 ④李纨评诗。 ⑤宝钗《咏螃蟹》解读。
经典语言及解说:1、“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
这是贾母说的话,“这个孩子”指宝钗。湘云开社作东,地点选在藕香榭,请贾母等前来赏花,贾母称赞一切安排得很别致。湘云说,“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贾母说,“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
这不是贾母第一次夸奖宝钗。第二十二回,贾母喜宝钗“稳重和平”。第三十五回,贾母当着薛姨妈和众人面称赞宝钗:“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笔者认为,贾母喜爱宝钗是真心的,一方面因为是亲戚,出于客气和礼节;另一方面因为宝钗“德、言、容、功”等方面都很优秀,符合贾母的传统观念和审美眼光。
贾母喜欢宝钗是事实,但是并不代表就有一定要让宝钗嫁给宝玉的想法。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2、“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
这是凤姐说的话。贾母开心,给众人讲了一件往事,小时候在枕霞阁玩,不小心掉进水里,虽然被救了上来,头上却被木钉碰破了一块,现在还留下一个指头顶儿大的窝。风姐不等人说,就开起了贾母的玩笑。
这件事不是什么好事,一般人不好接茬。但凤姐却能机变逢迎,应时即景,在贾母的“窝儿”上做起了文章。她抓住老年人都有的心思,称赞贾母是有福有寿的人。她把老祖宗比作寿星老儿,把贾母头上的窝儿,比作寿星头上的包儿。说那个“窝儿”是用来盛福寿的,等万福万寿盛满了,贾母又是一个老寿星。
王熙凤的这些话,把原来的坏事说成了好事,凶兆变成了吉兆,果然逗乐了贾母。贾母却故作嗔怪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得我撕你那油嘴。”宠溺之意溢于言表。
3、“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他这样,还这样说,他明儿越发无礼了。”
这是王夫人对贾母说的话,“老太太”指贾母,“他”指凤姐。贾母很喜欢凤姐,理由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凤姐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很会讨老太太的欢心。王夫人见贾母总是这样惯着凤姐,或多或少有点嗔怪的意思。
王夫人既是凤姐的婶娘,又是凤姐的姑妈,关系非同一般。她看不惯贾母溺爱凤姐,更看不惯凤姐没大没小,没轻没重的做法,觉得有失王家的家教。她这样说,也是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4、“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没的倒叫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
这是贾母对王夫人说的话,“他”指凤姐。贾母是贾府里辈分最高的人,她德高望重,受到晚辈们的尊敬。在对待晚辈方面,贾母不喜欢总是端着老祖宗的架子,反而对晚辈们比较宽容。
贾母不同意王夫人的说法,认为“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意思就是只要“礼体不错”,没有什么出格地方,在家里就应该随意一些,轻松一些,不要太过讲究和严肃。只有这样,“娘儿们”之间才能推心置腹,有说有笑,家庭氛围才能和谐快乐。
贾母认为凤姐是个知道“高低”的孩子,所谓“高低”,就是说话、做事知道深浅轻重。事实上凤姐是最知道眉高眼低的,每次开玩笑,分寸火候都把握得非常好,总能让贾母既舒服,又开心。
其实,贾母一直都不太喜欢王夫人,觉得她“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晚辈面前,王夫人就像个“神儿似的”,自己端着,被人供着,缺少生气,毫无情趣。这番话,也是贾母对这个木讷、古板的儿媳妇的教训。
5、“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
这是凤姐取笑鸳鸯的话。凤姐是出了名的醋坛子,对丈夫贾琏管控极严。这一次为什么会主动和鸳鸯开起这样的玩笑呢?是真话还是假话?
首先,鸳鸯是贾母身边的大丫头,深得贾母喜爱和信任。凤姐开这样的玩笑,或许是为了讨好鸳鸯背后的主子——贾母。
其次,鸳鸯掌管着贾母的小金库,凤姐和贾琏,也许眼睛早就盯上了鸳鸯手里的钥匙。
第三,凤姐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货色,或许她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她这样把话挑明了说,有意敲打一下鸳鸯也未可知。
第四,或许凤姐就是真心喜欢鸳鸯,把鸳鸯当姐妹待,觉得与鸳鸯投脾气,顺心顺眼,有意成人之美。
第五,或许这就是一处铺垫而已,为的是引出后文贾赦要娶鸳鸯为妾的情节。
6、“二奶奶来抢螃蟹吃,平儿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
这是鸳鸯取笑凤姐的话。鸳鸯是贾母的丫头,她的地位和普通的丫头不一般,随着贾母而水涨船高。凤姐见到她,也要敬重几分。这一次相互说笑打闹,就是凤姐先“没大”,挑起“事端”;鸳鸯后“没小”,加以“反击”。最后以凤姐求饶而告结束。
鸳鸯的取笑很精彩,她当着众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应时即景,编造了一出主子和奴才为了吃螃蟹而大打出手的情景剧,其中“抢”“恼”“抹”等几个动词特别生动传神。难怪贾母等众人听了以后都特别开心。
7、“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也有这个水亭叫‘枕霞阁’,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没了,你到底是旧主人。”
这是宝钗对湘云说的话。枕霞阁是史家原有的一座临水的亭子,与贾府的藕香榭差不多。这座亭子后来没有了,是因为年久失修坏了,还是被人为破坏了?小说里没有交代。有人猜测史家曾经历过重大变故,包括湘云父母的死,枕霞阁的没,似乎都在暗示什么。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想,没有任何证据。
探春说湘云也该起个号,宝钗马上就想到老太太说的“枕霞阁”,提议叫“枕霞旧友”。在小说中,宝钗是出了名的细心和敏锐。如第十八回,元妃把“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宝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提醒宝玉把诗中的“玉”字改为“蜡”字,以迎合元妃心意。第二十九回,张道士送给宝玉金麒麟,贾母说:“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随口答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细致入微的观察、无微不至的关心,这些本来都是宝钗性格中的优点,却被有些人过度解读,总说她是个别有用心的心机女。
8、“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然后《簪菊》《对菊》《供菊》《画菊》《忆菊》次之。”
这是李纨评菊花诗时说的话。李纨毛遂自荐,当了海棠诗社的首任社长。在她的带领下,海棠诗社成立初期的两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第一次咏白海棠,众人都说黛玉的诗为上,李纨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黛玉诗);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所谓“风流别致”,就是新奇巧妙,不拘成法,富有韵味,与众不同;所谓“含蓄浑厚”,就是包容内敛,淳朴敦厚,含而不露,耐人寻味。李纨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宝钗的诗写得“有身份”而评为第一。宝玉虽然提出一点异议:“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但是最终还是服从了李纨的裁定。
第二次咏菊花,李纨认为黛玉的三首诗《咏菊》《问菊》《菊梦》,“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分别获得第一、第二和第三。一个“新”字成为黛玉连中三元的致胜法宝。黛玉自谦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纤巧,细巧、小巧,即不够大气的意思。李纨说:“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意思就是巧得自然,不露痕迹。宝玉爱屋及乌,由人及诗,见自己的心爱之人独占鳌头,忘形地拍手叫道:“极是,极公道。”
两次“暗战”,宝钗和黛玉各胜一场,平分秋色。其实,这只是曹公独具匠心的安排而已。在曹公心中,宝钗与黛玉都是女神级的人物形象,她们不仅在爱情上、诗才上,而且在人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总是“两峰对峙,二水分流”(俞平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