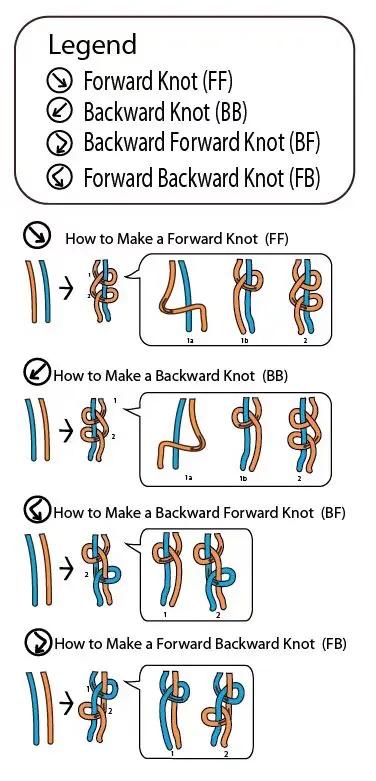邓中夏的最后一封信 不要哭要笑
1933年5月8日,他给狱中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称呼妻子“妹妹”。他写道,之前四封信你都没有回信,律师说你病了,没有见到你,信没有送到……不过现在好了,你已经病愈。

《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我可以放心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律师讲,他会转告给我。其余的事情,我照你说的做。好了,就是这样了。
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叮嘱“妹妹”要保重身体,要相信会有出狱的那一天,到那一天他们就可以团聚。
然而,他们的团聚却是在牢狱中。他们都带着脚镣和手铐,身上的血还没有干。他们面对面站着,他看见妻子笑了一下,自己也朝妻子笑了,说:“不认识。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他的妻子也说:“我不认识他。”
1933年9月21日,晨雾还没有散去,枪声打破了雨花台的寂静。
这枪声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地上的那个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对于这枪声,牢狱中的人已经不陌生了。
他们只是问彼此:“你们猜,这一次会是谁?”他们笑着。这笑声中没有痛苦,没有遗憾,只有胆量。因为他们知道,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声枪响。而他们都希望,听见这枪声的人不要哭泣,要笑。

《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此刻,地上的人已经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感觉。接着,枪声最后的回响也消失在了重新降临的寂静中。然而,这个人曾经活过,在那一天走向了雨花台,他的思想并没有消失,枪声并没有消失。这声音依然回荡在空气中。他最后的呐喊依然回荡在雨花台的上空。
历史的经典和尘埃 没有什么永恒
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就几个月前的7月25日,一场实力悬殊的海战在中国的历史上刻下了她两千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屈辱。
“济远号”和“高升号”在日本海军的炮击下缓缓沉没,舰船上的七百多士兵以身殉国。这场战役也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爆,同时也预示了一个东方古国的“沉沦”。
很多年以后,邓中夏才知道,当时的中国舰船要先进于日军的战舰。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中国战败的结果,并没有扭转清廷的毁灭。
战败四年后,戊戌政变又宣告着改革的失败,中国朝着深渊一意孤行。而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也无奈成为了清廷最后的筹码,让全体中国人看到的无非是权术的高超和两千年帝制积累下的“政治智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整整两千年的“智慧”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就化为乌有了。这时的邓中夏六岁,却开始念起了《千字文》和《三字经》。

《觉醒年代》中的邓中夏剧照
近二十五年之后,邓中夏还是能背出这些“经典”中的句子,但是他的声音已经不再有童年时的稚嫩,而是过早地变得沧桑——不断的街头演讲破坏了他的声带——而他的声音中也早已经找不见童年时的压抑。
也曾有人问过邓中夏,为什么在二十五年之后,他依然会记得那些文字。邓中夏性情豪爽,做事不推诿,他听后只是大笑,反而背诵得更大声了。他说,在自己上私塾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借着家里的煤油灯,温习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邓中夏所做的了——“东西”。那些经典也只不过是“东西”而已。他邓中夏为什么要在意一件东西呢?如果他忘记了,不是更糟糕吗?邓中夏于是留着这些东西,记住它们,看着它们在岁月中蒙上灰尘,失去原来的样子。
因为邓中夏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被灰尘埋葬,成为历史的灰尘——这不正是他在牢狱中对狱长说的话吗?他说了什么?你们这些人的末日就要到了,自己却还不知道,终有一天你们都将毁灭!那么,他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害怕的。
辛亥革命 湖南独立 邓中夏的激进和新潮
1911年,农历辛亥年,甲午战争也被之后十数年的屈辱所淹没。邓中夏进入了“高等小学”,继续学习经典。同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了起义。随后,七十二名勇士葬身黄花岗。

这是邓中夏第一次接触革命,也是他第一次听说“黄花岗”这个被他之后视作革命圣地的名字。只不过,当时十七岁的邓中夏不会知道,在二十二年之后,他会用自己的血祭奠另一处革命圣地。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随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10月22日,湖南独立了。
这段时期留在邓中夏的记忆中的却是“混乱”。在之后的岁月中,邓中夏回忆起清廷士兵的抵抗,回忆起中华民国军队的勇气,逐渐地,在邓中夏的眼中,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人都逐渐变成了一个人。
时间的刻痕不仅仅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邓中夏的思想,但是这改变却也让他迷惘了。事后,他回忆道,昨天还在背诵的经典,到了今天就是错的了,昨天的教书先生,到了今天就要剪了辫子……
然而,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邓中夏却被一股巨大的喜悦笼罩住了。他决定要参与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之中——考虑到邓中夏之后数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很难不让人想到他在十七岁时的思想转变——他慢慢地“偏离了”他所接受的教育,开始大量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

就是几个月之后,邓中夏的父亲目睹了自己的这个儿子和其他两位同学“桃园三结义”——他们同样叩拜,同样歃血宣誓。当邓中夏在喝下那碗血时,他的父亲知道终究有一天,自己的这个儿子会不再属于“邓家”。
1913年,十九岁的邓中夏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郴显的“联合中学”。他终于可以离开家了,也终于可以接受“西方教育”了。邓中夏并不否认自己当时的思想是“激进”的,也不想掩饰对曾经的私塾先生的“蔑视”。他蔑视的并不是经典——他怎么会蔑视一堆东西呢?——他蔑视的是过时的“价值体系”。
他的激进最终竟然容不下“联合中学”的西方教育,到了1915年,他离开了联合中学,用自己哥哥的中学毕业证书,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冒名入了学。然而,湖南师范学堂也没能满足邓中夏所追求的激进。
“那里和我想象的还不一样,”他事后回忆道,“没有那么激进,也不太新潮。”这就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讲出的话,而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湖南师范的教师们是用文言文授课的。

不过,有一位教师却成为了邓中夏真正的启蒙者,他就是杨昌济。这一年的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永远改变了中国人思想的版图。正是在杨昌济在家中,邓中夏看到了第一期《新青年》,也是在这位恩师的家中,邓中夏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
他们自然不会结拜,但是他们却都在《新青年》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他们也终于明白,只有激进是不够的,只有勇气是不够的。这时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仅仅在十年之后,他们三人将会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
4 时代的终点和起点 歃血不结义
如果说1894年7月25日开始的“甲午战争”是帝制中国的命运终点,那么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就是民主新中国的命运起点。
邓中夏真正参加“革命”正是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两年前,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并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打开了邓中夏的视野,有时他一整天都会待在图书馆里。

而图书馆的管理员正是邓中夏的中学同学,毛泽东。比他年轻一岁的蔡和森此时已身在法国,开始了漫长的勤工俭学生涯,并在两年后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出“要成立中国共产党”。
1919年5月3日深夜,邓中夏和谢绍敏依然在为第二天的有形做着准备——就在5月2日的“北大全体同学”大会上,谢绍敏咬破手指,在撕下的衣襟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他们共同制定了游行的路线,并且起草了这次游行的总纲领。
第二天下午一点整,邓中夏率领北大同学朝天安门进发。途中,一行人遇见了前来阻拦的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在他身后站着的是全副武装的军警。邓中夏上前和次长交涉,竟说服次长让了路。军警不敢动手,只得眼睁睁看着邓中夏高举“还我青岛”的标语从面前走过。

当邓中夏抵达天安门时,已经有数千名同学聚集在金水桥两侧。
在集会中,有人宣读了《北京学界宣言》。然而,这份宣言却是“希望西方民主国家为中国主持公道”,为中国出头,来抵制日本吞并青岛的野心……
——就在不到八年前,邓中夏还效法“桃园三结义”,喝下一碗血呢!可如今,他的“兄弟们”又去了哪儿?
这场运动留下了中国的悲哀和一团烈火。邓中夏也是火烧赵家楼中的一员。国家衰弱,青年们只好用这样的方式宣泄心中的痛苦和委屈了!邓中夏看着赵家楼的大火,心中的愤怒之火反而减弱,最后熄灭了。军警赶来了,将同学们逮捕。邓中夏逃过一劫,没有入狱。
在这一刻,邓中夏改变了。当天晚上他集合信得过的同学,开始商讨营救事宜。可他们最终发现,自己能做的也只是和北洋政府交涉。

可难道交涉会比游行示威更有用吗?邓中夏再次陷入了迷惘,他想起了辛亥革命,想起了湖南独立。如今,他在北京,却突然间明白了“革命”到底是什么。
还有远在巴黎的蔡和森。邓中夏又想到了曾经的恩师杨昌济,他曾经认为整座“联合中学”中只有杨昌济是“激进”的,可此刻他不这样认为了。他觉得自己也不再激进,也不再“新潮”了。毛泽东在哪儿?他会怎样看待自己今天的行为呢?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更本质的问题了。
入夜之后,邓中夏一个人离开宿舍,去了未名湖畔。他心中闪过一行诗句: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兄弟姐妹们,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我们去呢,不去呢?
5月7日,牢狱中的同学们被释放了。这时,邓中夏听说毛泽东正在组织湖南的群众运动,便决定前往湖南,投奔毛泽东。他有两年没有回过家了。
5 邓中夏的家庭 魂断雨花台 最后一张合影
在家中等着邓中夏的除了他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他的妻子杨怀贤。邓中夏是在父母之命下和年长自己两岁的杨怀贤结婚的。
邓中夏从没说过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这场包办婚姻不仅伤害了邓中夏,更是伤害了杨怀贤——杨怀贤一开始是被安排嫁给邓中夏的哥哥邓隆泮的,但是在结婚之后,邓母发现他们八字不合,便在1908年将杨怀贤嫁给了邓中夏。这一年,邓中夏只有十四岁。
当天晚上,邓中夏和杨怀贤同房。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家乡。
这次回去,邓中夏也是为了和杨怀贤离婚。杨怀贤没有反对,同意离婚。这一年,她二十九岁。离婚后,杨怀贤留在了邓家,照顾邓母和邓父,一生再未结婚。

邓中夏的第二任妻子叫李慧馨,做过“童养媳”。邓中夏在1925年和李家的这对兄妹住在同一所公寓内,便逐渐熟悉了。第二年的8月,邓中夏和李慧馨结婚。之后的七年间,李慧馨同生下四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在出生后三天夭折,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寄养在乡下,之后失去了消息,虽然四方寻找,但终究没有找到。
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由于工作调动频繁——李慧馨是上海地下党最机密的无线电台工作——李慧馨无法照顾孩子,不得不将孩子送人,之后便音讯全无。最后一个孩子留在李慧馨身边七个月。
1929年冬天,李慧馨带着五个月的孩子穿越“满洲”封锁,进入苏联和邓中夏团聚。两个月之后,这个孩子染上肺炎,死了在苏联。一年后,邓中夏就离开苏联,回到了中国。
1931年夏天,邓中夏失去了在党内的所有职务,在苦闷中度日。6月,他听说蔡和森被捕。可他已经无能为力。
8月4日,蔡和森死在了广州的军政监狱里。这时的邓中夏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快要走到了终点。他们都要将生命献给这个国家了。然而,还有更大的苦难在等着邓中夏。1931年11月3日,他得到了妻子李慧馨被捕的消息。
1932年秋天,“赋闲在家”的邓中夏突然被调派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半年之后,他在法租界被巡捕逮捕。
他和李慧馨最终便以这种残酷的方式相见了,然而他们却又不能相认。邓中夏还在狱中遇见了曾经的战友陶铸。陶铸问他“有什么打算?”。
邓中夏指向雨花台的方向,说那里便是他要去的地方。
1933年9月21日,天色尚暗,邓中夏死在了雨花台。不会有人知道他最后想到了什么,又想到了谁。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他想到了妻子李慧馨和他们的孩子。

我更愿意相信,邓中夏想到了1929年2月10日这一天。他和妻子带着五个月大的孩子去了住处附近的一间照相馆,拍下了这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那一天的莫斯科下过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