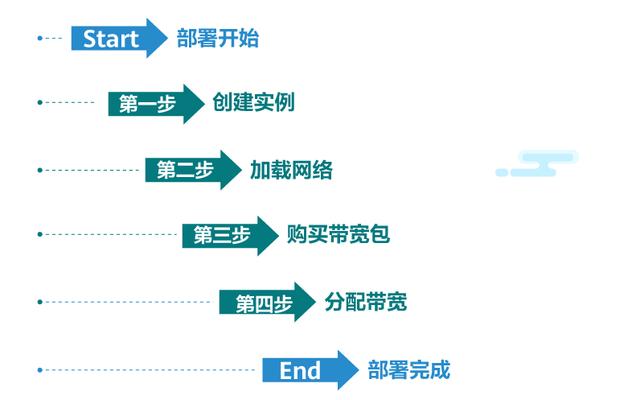【原文】
子曰: “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 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
■ 张居正直解 道,是道理,当然。处,是居处。去,是避去。孔子说: “ 人之所遇,有顺 有逆,然取舍之间,贵于审择。且如富与贵这两件,是人人所愿欲,谁不要得而 处之,然有义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应得的,虽处之亦无不可,设使无功而 受禄,无德而居位,不应得富贵而偶得之,这便是无故之获,有道者所深忧。君 子见利思义,决然辞之而不处也,其能审富贵如此。贫与贱这两件,是人人所厌 恶,谁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该得的,其顺受固不待 言,就是学成而人不见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应得贫贱而偶得之,这也是适然 之数,于身心上无损,君子乐天知命,决然处之而不去也,其能安贫贱如此。 ” 审富贵则可以处乐而不淫,安贫贱则可以处约而不滥,非修德体仁之君子,其孰 能之。孔子说: “ 审富贵,安贫贱,不徇欲恶之情,而惟要之于理,这是仁之道。 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异乎人者,以其有此实也。若于富贵则贪之,于贫贱则厌之, 但徇欲恶之私情,则舍去此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叫作君子。仁之不 可去也如此。 ” 终食之间,是一顿饭的时候。违,是违背。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时。颠沛, 是倾覆流离之际。是字,解作此字,指仁而言。孔子说: “ 去仁不可以为君子。 ” 所以君子之为仁,不但处富贵贫贱而不去也。自至静之中,以至应物之处,自一 时之近,以至终身之远,其心常在于仁,未尝有一顿饭的时候,敢背而去之。虽 造次之时,急遽苟且,当那等忙迫,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虽颠沛之际,倾覆流 离,遭那等患难,他的心也只在这仁上。夫当造次颠沛而其心犹在于仁,则无一 时而不仁矣!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夫君子存养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 处富贵贫贱,又岂有不得其道者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子曰: “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所想要的,但如果不是正道得来,那我不要。 这不一定是捡来、偷来、骗来、抢来,而是说那不是我该得的,它自己来了,那 我 “ 不处也 ” , “ 处 ” , 安住的意思,我不要,因为不能安处这富贵。 比如是人家给的,但我觉得我不该得,是不是他搞错了呢?心中不安,不能安处。 这就像前面说的 “ 吃亏论 ” , 不怕吃了别人的亏,就怕不小心让别人吃了自己亏。
不怕没得到该得的,就怕拿了不该拿的。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反过来,贫贱是人人都不喜欢的,人人都想摆脱贫贱,但如果以不义之道脱贫, 那我还是不要脱贫吧! 总之是安贫乐道,审富贵而安贫贱。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如果违背了仁, “ 恶乎成名 ” ? 那怎么能被称为君子啊? “ 终食之间 ” , 一顿饭工夫。 “ 造次 ” , 匆忙。 君子没有一顿饭的工夫是违背了仁的,匆忙急遽之时仍是仁,颠沛流离之时仍是 仁。从富贵、贫贱的取舍之间,以至于穿衣吃饭之常、匆忙急遽之时,颠沛流离 之中,也不会 “ 去仁 ” , 不会放弃仁。 我们有时候会说: “ 喂!我跟你说!我不管了哈! ” 这时候是啥?不管啥?事实上 就是准备 “ 去仁 ” 了,不管什么仁不仁了。给自己壮胆,准备干坏事,伤害他人。 所以孔子用了 “ 去仁 ” 两个字,深可玩味。不是要你 “ 取仁 ” , 而是叫你不要 “ 去仁 ” 。 因为仁本来就在你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