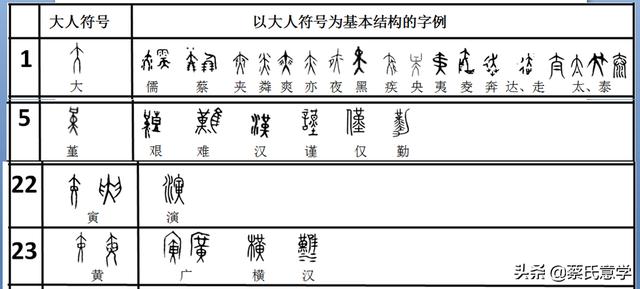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万丈,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洒脱。
他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柔浪漫,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缱绻深情。

同样的天纵之才,比之李白,他多了几分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样的命运多舛,比之杜甫,他又多了几分乐观旷达的心态。
从眉州到汴州,他历遍了人生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从惠州到儋州,他也受尽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举杯提箸,便带起了满身的人间烟火,挥毫泼墨,又占尽了尘世的绝顶风流。
人生如逆旅,他竹杖芒鞋的身影在时光中轻轻走过,两宋三百年的绝代风华,才最终成就了一个光耀后世的名字——苏东坡。
眉州:用神话的开头为天才加冕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冬天,四川盆地西南、岷江之畔的风雅小城眉州,一个名叫苏轼的男婴呱呱坠地。
据说其出生前一年,家乡附近的彭老山便开始百花不生、草木枯萎,连鸟兽亦避走它处,直到多年后当地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此地灵气尽被苏轼一人吸走。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王侯将相诞生,必然伴随天地异象,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便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宋太祖赵匡胤降世时,也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
类似这种声、光、电毕现,色、香、味俱全的离奇故事,似乎是专门为了证明大人物们的“生而不凡”、“天命所归”而添加的注脚,而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叙事风格,也几乎成为后世史书的惯用笔法。
但九百多年前彭老山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气运流转,或许并非出自史家事后的刻意编排,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大自然对这位中国数千年来独一无二的天纵之才,所给予的绝无仅有的慷慨馈赠。
长子苏轼出生两年之后,1039年,苏家又迎来次子苏辙的降生。父亲苏洵为两个儿子取名都与“车”相关,其中也是大有深意。
车舆,通常为负载之物,而承载万物的大地,自然便是最大的车舆,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苏洵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辙。
只是苏洵可能也没有想到,“轼”、“辙”这两个字,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兄弟二人一生的命运。
“轼”是车上的扶手,是整架车最显眼、装饰最华丽的部分,苏轼天纵之才,无疑是两宋最耀眼的风流人物。

而“辙”是车辆碾压后留下的痕迹,虽与车的本体并无关联,但无论车辆发生怎样的灾祸,车辙都不会被殃及池鱼。
所以,“木秀于林”的苏轼,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而与兄长相比,苏辙的才情虽稍逊风骚,但仕途却相对平顺,不似其兄一生坎坷、颠沛流离。
汴州:他一出场,便惊艳了时光仁宗嘉佑二年(1057),苏洵陪同苏轼、苏辙兄弟由眉山老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当苏轼第一次出现在开封街头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会在今后的文坛掀起怎样的滔天波澜。
1057年的进士科,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均在此科及第,而且还涌现出了九位宰执和大批顶尖学者,因此也被后世公认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令主审官梅尧臣拍案叫绝之余,其中又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样的佳句。
作为整篇策论的支撑性论据,这个皋陶欲杀人而尧劝其宽恕的典故,论点清晰、论据充沛,且用典十分到位。
梅尧臣虽倍感精妙绝伦,但饶是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儒,脑海中穷尽四书五经,一时之间也不知典从何来。
连忙将此卷送至另一主考官员,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共同审阅。
从宋朝开始,所有科举试卷均采取“封弥”这一保密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用纸糊住,以保证阅卷的公平。
苏轼的文章欧阳修内心也是大加赞赏,但其暗忖如此锦绣文笔,很有可能出自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免嫌疑,欧阳修只得将这份理应独占鳌头的试卷判为第二。
不过颇为尴尬的是,放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原本位列第二、如今高居榜首的,正是其弟子曾巩,而那篇精妙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位叫苏轼的四川举子之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梅尧臣问及文中典故出自各处时,苏轼的回答竟然是“想当然尔”。
虽是杜撰却毫无造作之处,信手拈来却又浑然天成,苏轼的惊才绝艳和不拘一格由此也可见一斑。
1057年的礼部会试,虽然在阴差阳错下与“会元”擦身而过,但初出茅庐的苏轼牛刀小试便已然锋芒毕露。
而这个眉山青年的才情更是令欧阳修、梅尧臣这样的文坛领袖都赞叹不已。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和再三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每逢其新作出炉,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只是苏轼身上的奇迹仍在继续,1061年,他又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入三等”这一惊人成绩。
制科考试,是为国家选拔“非常之才”而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
与科举考试相比,参加制科不仅需要有公卿大臣推荐,而且录取率极低,有宋一朝,进士及第的人数大约有四万人,而成功通过制科考试的只有区区四十一人。
考试成绩虽有五等,但一、二等实际都是虚设,苏轼“入三等”的成绩,在整个宋朝的制科考试历史上,也仅有四例,苏轼之前百年,更无一人得此佳绩。
虽然说“文无第一”,但仅就应试能力和科举文章而言,苏轼也绝对是两宋最顶尖的人物。
杭州: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但正当苏轼准备大展拳脚之时,1066年,父亲苏洵不幸病逝,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为父守孝三年。
待到丁忧期满,苏轼重新回到朝堂之上,已是1069年。此时,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苏轼虽然文采风流,但其政治观念却偏向保守,主张循序渐进,面对王安石大开大合、急于求成的改革手段,他内心极为抵触。
彼时,其初入官场,毫无根基,却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政治心态又极不成熟,竟屡屡上书痛陈变法之弊端,甚至利用自己任国子监考试主考官的机会,出题嘲讽王安石蒙蔽圣上,独断专行。
很快,“愤青”苏轼就为自己的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熙宁变法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又深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与“拗相公”宣战的结果,是神宗对其数次的重要提拔,都在王安石的坚持下遭到否决。
而变法的支持者和王安石的拥趸们,更是借此机会对苏轼进行不遗余力地攻讦。
朝堂这个是非之地,眼见已难立足,再待下去,则恐有引火烧身之虞。
因此,苏轼主动申请出京任职,而神宗尽管对其才学非常欣赏,但无奈苏轼终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得同意将其外派至杭州任通判。
三年杭州通判任期结束后,苏轼再次请调密州任职,在此期间,一篇《江城子 · 密州出猎》不仅让密州名扬天下,更是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
从1071年开始,苏轼参与主持地方工作长达八年,先后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三地知州,而这八年的时间,苏轼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尤其是1086年,第二次出任杭州知州时,苏轼致力于当地的市政建设和民生发展,修建水利、疏浚西湖,又利用挖掘的淤泥和杂草堆筑出了著名的“苏堤”,更为杭州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

地方上的政绩斐然,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绝非纸上谈兵之辈,他不仅写得出针砭时弊的策论,更当得好忧国忧民的父母官。
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并按照惯例向皇帝呈上谢表。
岂料这道《湖州谢上表》,不仅给苏轼带来了牢狱之灾,更深刻改变了其此后的整个人生。
黄州:大江东去,东坡新生“谢表”原本不过是官场上的例行公事,格式、内容几乎都有固定的模板。
但已年逾不惑的苏轼,仍不改当年的愤青本色,在对皇帝表达感谢的同时,又夹枪带棒地发了几句牢骚。
很快,苏轼的谢表就在朝堂之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弹劾其讥讽新政,一石激起千重浪,御史舒亶、李定,国子监李宜之等人随即群起而攻之,攻击的对象也由最初的谢表迅速扩散到针对苏轼的所有文学作品。
而客观地说,苏轼之前的诗文,部分内容确实有抨击新法的倾向,给了别有用心之人以口实,而更关健的是,一旦调查取证的范围扩大,过分解读、刻意的歪曲事实和污蔑,必然是防不胜防。
苏轼被弹劾的罪名,也由最初的“讥讽新政”逐渐升级为“蛊惑人心”直至最严重的“诋毁圣上”。
而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面对朝臣汹涌而来的奏折,以及从苏轼文章中找到的如山铁证,宋神宗再爱才,也只能将苏轼移交御史台审理。由于御史台上遍植柏树,常引来乌鸦栖息,因此也被称为乌台,而“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一生最大的劫难,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
就这样,本来刚准备在湖州开始新生活的苏轼,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为了阶下囚,此后更差点被判处极刑。

好在不少保守党人为苏轼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宰相吴充等人亦出面力保。甚至连之前的政敌、已经卸任宰相的王安石也施以援手,连夜上书神宗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加上宋朝不杀文人的祖训,神宗最后才赦免了苏轼的死罪,将其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
但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黄州的这个地方小官,既无实权,更乏俸禄,只不过是个挂名在当地、受监督的犯官。
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贬谪落寞的戴罪之人,苏轼还来不及感叹世事无常,就要抓紧时间解决穿衣吃饭的现实问题。
面对生活的困窘,苏轼主动向黄州官府申请了五十亩荒地,因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之外,苏轼称其为东坡,而自称“东坡居士”。
在放下身段从事劳动生产的同时,苏轼也在深刻反省自己前半生的愤怒、尖刻,心灵的寄托由官场名利转移到对大自然山水的流连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其精神境界更是由具体的政治忧患升华到宽广的人生思考。

走出官场失利的阴影,苏轼的心境愈发豁然恬淡,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苏轼的闲情逸趣继续发展为对口腹之欲的热爱,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美食相继诞生。
而黄州四年,不仅是苏轼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其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1082年,他来到黄州赤壁矶,面对滚滚江水,感怀历史、人生,展开歌咏,苏轼的千古绝唱、宋词中震烁古今的伟大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由此横空出世。
1082年春,偕友郊游遇雨,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更是完美诠释了其逆境之中超凡洒脱的人生态度。
大江东去,曾经疾恶如仇、桀骜不驯的苏轼成为了历史,人间却从此多了一个更加成熟、旷达的坡仙——苏东坡。

1084年,神宗思虑人才难得,将其由黄州改判汝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应苏轼的申请,许于常州居住。
前往常州赴任的路上,苏东坡主动提出要拜访归隐金陵(南京)的王安石,而年逾花甲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更是亲自到江岸渡口迎接。
此时的苏东坡早已洗尽铅华,而执拗、强势的王安石,本也是光明磊落之人,千帆过尽之后,两个曾经互相敌视的对手,终于在长江边“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昔日的恩怨冲突,不过是因政见不同而引起的意气之争,此时的握手言和却代表着当世两大卓绝人物的惺惺相惜。
暂居金陵的日子,二人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品茗饮酒,不亦乐乎。苏东坡为王安石的气度、见识所折服,而道别之际,望着苏东坡离开的背影,王安石更是不禁感慨:“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只是苏东坡在常州盘桓不久,朝堂之上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85年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哲宗冲龄践祚,高太后临朝听政,并请出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出任宰相。
司马光上任之后,大批旧党官员被启用,而备受其器重的苏东坡也是其中一员。
从1085年5月到1086年9月,苏东坡的官职一路擢升,由朝奉郎、登州知州、礼部郎中直至翰林学士,短短十七个月,便由一个偏远地区的犯官迅速擢升为朝廷的三品大员。
这是仕途坎坷的苏东坡在官场最为辉煌的时刻,但辉煌过后却没有迎来人生的顶点,反而是更加迅速地坠落。
因不满司马光及其党羽对新党的打压和全盘否定,耿介忠直的苏东坡,再次上书直谏,并抨击了旧党执政的腐败现象,由此引起了保守势力的针对和陷害。
再加上此次苏东坡重回京师,本是怀着一腔热血,单纯地想为国为民做一点实事,他无意于加入任何的政治、党派的争斗。
1089年,苏东坡再次自请外调,出任杭州知州,如果说1071年第一次请调杭州时,其政治上是失意的,内心更是充满了苦涩与愤懑,那么时隔十八年后,却是看破官场丑态后洒脱的抽身,甚至还有几分脱离泥潭的兴奋和欣喜。
但正所谓人生无常,元祐八年(1093),旧党靠山、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十六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的变法主张,新党抓住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

苏东坡也因为一直以来身上旧党的标签,而再次遭到贬谪,1094年,先是被贬岭外英州(广东英德),尚在赴任途中,又再次接到圣旨,转徙惠州。
远贬惠州的日子,相当困窘,但对于饱经风雨的苏东坡而言,生活的磨难早就习以为常,乐观洒脱的他,依然过着清贫而悠然的生活。
不仅如此,并无实权的他,还多方奔走,最终促成了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当然,才华横溢又爱好美食的东坡居士,又在当地爱上了荔枝这一美味水果,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更是成为千年以来宣传岭南风物的最佳广告。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再次遭贬,这次是更远的海南儋州。
当时的海南,可以说是人迹罕至、烟瘴丛生之地,但被一贬再贬的苏东坡,听闻胞弟苏辙被贬雷州,竟相当幽默的写下了“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的诗句。
就像多年前,挚友王定国的侍妾柔奴对其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面对逆境坎坷,悲欢离合,苏东坡早已释然。
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并大赦天下,苏东坡终于结束了七年的贬谪生活,北返中原。
而闻知苏轼北上,要经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成千上万的百姓,纷纷自发随船前行,竞相争睹这位人中龙凤的绝世风采。
然而此时正值盛夏,暑气蒸腾,苏东坡又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下,最终染病不起,公元1001年七月,北宋最卓绝的天才,一代文坛巨星,在常州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