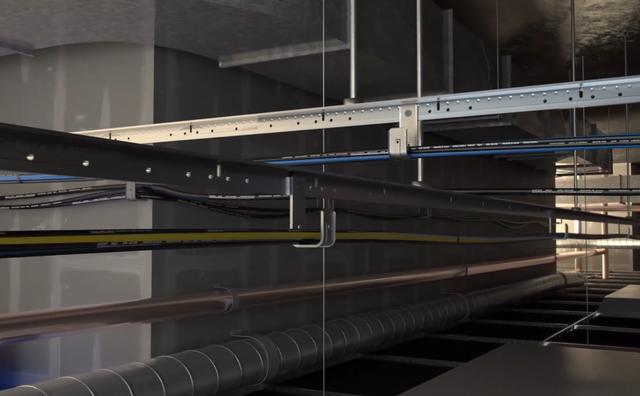作者:Cjl1949 来源:美篇App

五弟唯一的遗像
我的小弟弟,乳名小民,学名陈继德,生于1957年,在家排行老五,平日亲切地叫我“大哥哥”。
农历九月初十是我的生日,也是五弟的生日。弟弟比我小8岁,如今我已年逾花甲,而小弟弟却在九泉之下50年了。
50年来,弟弟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也一直怀念着苦命的小弟弟。
50年来,小弟弟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悲痛,无已的思念和无尽的泪水。
每年清明节和过年尤其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小弟弟的音容笑貌就会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悲痛和思念之情就揪住了我的心。别人在欢乐中度过的幸福时光,却成了我在悲哀中熬过的痛苦日子,每当想起小弟弟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弟弟和我自小相依为命,又因为是同一天生日,同胞兄弟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幼年的小弟弟伴我度过了童年,小弟弟对我的依恋凝聚的是血浓如水的深情;我悲叹苦命的小弟弟,命运给予弟弟的全是不幸,从出生到去世,短短的六年,苦了六年,可怜巴巴地苦了一生。

每次我想起小弟弟,眼前就会显现出小弟弟清晰的面容,耳边仿佛响起了小弟弟稚嫩的童音,脑海中就浮现出小弟弟活泼的身影,以至使我悲痛不已,泣不成声。
小弟弟未出生时,母亲就患有重病。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善良、勤劳、淳朴、贤惠、有文化而又有修养的大家闺秀。
为了我们这个家,她任劳任怨,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的日子。她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受尽了一个女人难以忍受的苦和累。她知书达理而又少言寡语,既会过日子,又疼爱孩子。不管邻居、亲戚朋友、还是本家族人,谁都夸母亲是个贤淑而又勤快的人。由于家计艰辛,操心过度,终使母亲积弱成疾。
母亲在怀有小弟弟前就得了气管炎、心脏病、胃病、结核病……最主要的还是精神病,发起病来生疏不辨,整天不吃,不喝,不睡,生活不能自理。全家人对母亲遭受的痛苦都有说不尽的心痛。
都说是“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可由于母亲常年有病,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多病的母亲又牵掣着他的大部分精力,这就注定了我那可怜的小弟弟是个苦命儿。

我们兄弟5人,大哥二哥已成家立业,我与两个弟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人们常说 “天下爷娘爱小儿”,可在我们这样一个弟兄众多的家庭里,小弟弟一出生,就没享受到应有的母爱,也没得到父亲的特别呵护。
小弟弟6岁那年因患急性脑膜炎离世,病程很短,患病时虽然症状明显,却因多种原因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年幼夭折。
父亲是我县家喻户晓的名老中医,治疗病势凶险的急性传染病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尤其是治疗温热病,在我们那一带,可以说独步当时。 若不是那艰难的年代,按理说,小弟弟出生在中医世家,不应该年纪轻轻地就命丧黄泉。
小弟弟去世后的第二年秋末,跟着嫂子住在康庄公社李家庄的侄子得了急性脑膜炎。听大嫂说,那天下午两点多钟,侄子突然发高烧,头痛如裂,呕吐不止,浑身抽搐,角弓反张,一会就牙关紧闭,不醒人事了。嫂子和她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李进义急急忙忙地把侄子从李家庄抱到我家时就已近黄昏。
那晚上,父亲和大哥大嫂整宿没睡。父亲用筷子把侄子的牙关撬开,一夜之间连续灌了11次中药。第二天凌晨,侄子才缓过气来,睁开眼时嘟囔了一句:“爸,我怎么看不见了。”大哥大嫂吓得嚎啕大哭。父亲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判断出没什么大问题,安慰他们说:“不要紧,这是因为长时间高烧不退,一时视力失明。恢复恢复就好了。”果然住了不到10天的时间,侄子的身体各个方面包括视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那年,侄子患了和小弟弟同样的疾病并且病情比小弟弟还严重得多,但父亲凭着精湛的医术,把自己的孙子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我们刚吃早饭,堂姐来我家对父亲说:“叔,您看看小纪怎么的?”父亲说:“吃完饭我就过去。”听姐姐一说,我马上放下筷子就跟着过去了。自弟弟去世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学好中医,五弟的悲剧在我们家族中不能再重演了。我来到堂姐家,看到外甥小纪正发高烧,抽风,呕吐,牙关咬得紧紧的,就赶紧跑回家,对父亲说:“小纪可能得了脑炎。”父亲一听急了,饭也顾不得吃,撂下筷子,急匆匆地跑过去,看完了病,紧接着安排人去买药。买回药之后,连续灌了几次,抽风等凶险症侯逐渐消失,两天就脱离了危险期,调理了几天就康复了。至今侄子和外甥都很健康。那次差点要了命的病,都没给他们俩留下丝毫的后遗症。每当看到侄子和外甥,我就想起了五弟,心里就越发难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命运给予弟弟的全是不幸。弟弟出生不久,全社会就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的1958年。那个年月,中国人是记忆犹新的,大炼钢铁、卫星上天创高产、日行千里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尤其人民公社化后,卫生院、敬老院、幼儿园、公共食堂、群众活动室、贫下中农协会等等遍地开花,有组织就需要场地办公室,集体没有房子,怎么办?只有占用民房。我家8间房子,被南关大队占用后做了托儿所。襁褓中的弟弟也遇时逢殃,随全家搬到张建儒家。
张建儒家住傅家大街西头路北,家里有5口人。她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儿子,5个人原先住着3间屋,我们搬去后两家9口人挤在3间二十左右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住东间,他们住西间,两家共用一间厨房。本来就不宽敞的空间我们搬去后就更加拥挤了。那时候,不管你能不能住得开,不管你有没有办法住,没有商议的余地。幸亏我家没有什么家当,除了放粮食的小缸(其实缸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就是一个箱子和一个盛衣服的柜子。做饭的锅都被砸碎炼了钢铁,不需要安锅灶,即使安了锅灶也用不着,全村人都吃集体食堂,不用自己做饭。
我家虽是街道户口,但也要到村办食堂吃大锅饭。村里根据人口多少发了自制的粮票,我们吃的饭,每次都是我去食堂排队后领回来的。公共食堂不到时间不开饭,家中丁点儿吃的也没有,母亲连病带饿没有奶水,弟弟饿得哇哇哭,急得母亲直流泪。看着弟弟可怜巴巴的样子,望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想想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家庭,我心里有的只是难受和万般无奈。

最难熬的是1959年。这年,我母亲再也经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生活的折磨,病情越来越重。可就在此时,父亲却在省城开几个月的政协会,又上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这就使本来无人照料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大哥大嫂在乡下,二哥在沂水教学,二嫂在被服厂上班,家中就只有我、弟弟和母亲。
母亲卧病在床,弟弟刚刚蹒跚学步,我还得上学,实在没人照顾我这可怜的小弟弟,没办法我只好白天把他送到姥娘家,晚上放学后再把他从姥娘家接回来。
姥娘家住东关断魂桥东边一个很深的胡同里。胡同左拐右弯的有二百多米长,只有一米多宽,两边高高的房子,夹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即使白天也是阴森森的让人害怕,晚上就更少有人走。路面是乱石铺的,被雨水冲得东一块西一块的,走在上面绊绊磕磕。
10岁的我,长得不过1米2高,不仅体力弱,而且胆量小,怕鬼。其实心中也确信没有鬼,可总是驱除不了那种恐惧感。我接着弟弟扛在肩上,一踏进这阴暗逼仄的长胡同里,头皮发麻心就七上八下地怦怦直跳。心里很矛盾,盼望有人出现,还怕碰到人。偶尔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心里就发毛,就像觉得那声音不是人走动发出来的。黑洞洞的胡同大部分时间都是像死一般地沉静。我攥紧弟弟的小手,试探着往前迈步,恐怕被石头绊倒,更怕的是忽然有什么东西窜出来。有一次,一只毛茸茸的东西突然从脚边溜过去,吓得我浑身出汗,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差一点就摔倒。过后想想肯定是只猫,可是我把它想象成了黄鼠狼或狐狸之类可怕的动物了。
每次走进这令人胆颤心惊的胡同时,我就凭着和不到两岁的弟弟拉呱来驱赶内心的恐惧。我问这问那,东扯西拉,弟弟有问必答。弟弟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一个劲地用他那稚嫩的童音,不成句子的话语,讲述在姥姥家一天的故事,完全沉浸在见到大哥哥的快乐里。每当此时,我虽然害怕,但看到弟弟那欢快的样子,心中便充满了一种幸福感,真有和弟弟相依为命的感觉。我想,我和弟弟深厚的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在我童年的生活里,在那苦涩的日子里,是弟弟给了我一丝甜甜的欢悦。
我年幼体弱,肚子饥饿,扛着弟弟,走完了从姥娘家到我家的二里多路,连累带吓,浑身总是湿漉漉的,有时又觉阵阵晕眩。到家后,我把弟弟放到炕上,顾不得喘息,就得给母亲煎药。虽然父亲不在家,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母亲开的药方,但母亲每天都要吃药。我支起药罐,点上火,屋子里充满了浓烟,母亲呛得直咳嗽,弟弟在一旁哇哇哭。母亲那种病和一般病人不一样,刚煎出的药太热,她不喝;煮的时间长了药就凉了,又不喝,再温。一晚上经常折腾到半夜。弟弟要睡觉的时候就要闹一会,我就抱着弟弟煎药,温药。那时候一天三顿饭到食堂吃,家里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弟弟饿着肚子睡觉,母亲饿着肚子生病,我饿着肚子煎药、哄弟弟、伺候生病的母亲。好在我的弟弟最听我的话,不久也就睡着了,看看弟弟那饥饿的样子,母亲那凄苦的神情,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到了冬季,父亲开会回来了。父亲一进门,我看到半年多没回家的父亲,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觉得有了主心骨,浑身一下子轻松了。心情一激动,泪水在我眼眶里直打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淌下来。可能是觉着受得委屈太多,也可能是觉得现在有依靠了,那天晚上,我吃了一顿从来没感觉那么好吃的饭。父亲捎回一些能下锅的点心,家里也生上了炕炉子,坐上铁盆子把点心放上一煮,我和弟弟每人分了一碗,我们吃的那样香甜,弟弟连碗都舔得干干净净。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我和弟弟吃到了一生最香醇最甜美的晚餐,度过了一生最温暖最幸福的一夜。
父亲回家后,我家的住处立时就有了改观。因父亲是民主人士,县政协副主席,共产党团结的对象。县里统战部门出面找了南关大队,在傅家大街路南安排了五间大瓦房。院子不小,还有后院,房子的主人叫单代。他在外地工作,房子村里管着,也没和他们打招呼,就安排我家住进去了。
第二年,单代的夫人到我家找过我父亲,要300元钱卖给我们。5间大瓦房300元,连个白菜价也不值,但父亲不要。那个吃了上顿还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下顿的年代,谁还有心思置办房产,何况我家还有8间房子被大队里占着。以后虽然托儿所停办了,但大队也没有把房子退给我们的意思。西屋那两间,先后又把张聿俭和单秀峰家安排进去了。东屋3间当了仓库,放了些氨水罈子,墙皮都被腐蚀坏了。正屋5间,后面还有3间西厢屋,原先是我父亲开药舖用的。我们搬家后被大队里拆了,据说盖了场院屋。
那个年代,有理的人被说成无理,无理的人硬说自己有理。自己的房子被生产队里占用后,已经不用于所谓的公共事业了,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把房子退给人家。幸亏父亲是共产党的朋友,以后又由统战部门出面找大队交涉,我们就搬回去了,那是后话了。

搬进单代家以后,家境更加贫困,母亲病情加重,整天饭不吃,觉不睡,舌苔黑厚干燥,嘴唇干得暴皮,瘦得皮包骨头,两眼瞪得直直地,样子很吓人。全家人都担心母亲恐怕经不住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了。母亲这病最怕刺激,受不得压力。那年头,吃没的吃,喝没的喝,住处没有着落,父亲作为民主人士,在那种政治形势下,也只能忠心耿耿服务国家。家里只有一个不顶事的孩子,还得照顾着另一个处处得用人的更小的孩子,钱没有钱,东西没有东西,谱没人帮着打,就是健壮的女人也就崩溃了。何况我母亲本来就有病,体质弱,老实内向,有苦咽在肚子里,病情不重就怪了。
由于我得上学,父亲还要上班,弟弟在家没人照顾,凄苦无奈的父母,只有让两岁多的弟弟过起了寄居生活。先是住在二嫂子娘家,后又住在我姑家表姐王淑德家。弟弟住在别人家里,带去了我的思念与牵挂。这时,我真的尝到了亲人分离的痛苦滋味。放学后我就去看他,见面后亲得不得了,弟弟搂着我大哥哥长大哥哥短地叫个不停,难受得我直淌眼泪。二嫂娘家和表姐家对弟弟照顾得非常好,时间不长,弟弟的小脸就红润润的胖乎乎的了。在那极端困苦的年代,二嫂娘家和姑表姐家能把弟弟照顾得那么好,多么不容易啊!他们是一点一点从口中省出粮食来抚养弟弟。看看这些善良的人家,想想他们对我家的恩情,至今我都感激不尽。
把孩子长期放在别人家寄养也不是个办法。第二年春天,正是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弟弟被送进了县托儿所。每月12元托管费,弟弟在粮证上12斤粮食的指标也给了托儿所,由托儿所直接到粮管所买粮。弟弟上托儿所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可我一想到我不能随便去看弟弟,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我是多么舍不得让弟弟离开我啊。

终于盼到了两个星期以后的星期六下午,父亲叫我把弟弟领回来度周末。看来母亲也想孩子了。我放下书包,一口气跑到了托儿所。可我一见到弟弟,立刻惊傻了,弟弟入托的时候,小脸红红的,圆圆的,胖胖的。两个星期没见,脸却变得清瘦而有些煞白,一丝笑容也没有,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大哥哥”。这就是我亲爱的小弟弟?十几天里,你是怎么生活的?我赶紧把脸背过去,强忍住泪水不让它流下来,鼻子却一阵阵的发酸。
出了托儿所,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弟弟,在托儿所能不能吃饱了,老师打人不,两个星期才去接你,同学不欺负你吗……我知道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每到星期六就接回家。一个才不满3周岁的孩子看到别人的爸妈都把自己的孩子领走了,只有他一人孤伶伶地在那里,心里是什么滋味?有谁能理解一个孩子身心的创伤和苦痛,又有谁能体会到一个幼小的心灵的孤独与悲哀?可任凭我怎么问,弟弟就是一声不吭。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没有了昔日亲情,连急于回家见到亲人的兴致也不存在了。
看到弟弟一脸的漠然,一脸的悲哀,我的心痛极了,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两个星期的县托生活,弟弟竟像变了一个人。

拐过南关街路口,走到苗秀石的门口时,弟弟突然挣脱了我的手,往前紧跑了几步,飞快地把地上的一块胡萝卜把儿抢起来,用小手擦了两下,塞在嘴里嚼了三两下伸着脖子就咽下去了。看着弟弟噎得眼里淌泪,我盈满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哗哗地流了下来。一直到接弟弟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弟弟在托儿所的生活连家里也不如!那时,我们在家里用胡萝卜做小豆腐,还能填饱肚子,不用定量。可从弟弟的行为来看,胡萝卜已是他生活中的奢侈品。难怪弟弟在回家的路上,眼睛不住地四处张望,根本无心和我说话。
因为弟弟回来了,那天家里吃了顿比平日要好的中午饭,除了用胡萝卜做的小豆腐之外,煮了一些地瓜,用粗麦子面做了几个饼子。饼子是给弟弟和父亲吃的,我们吃地瓜和小豆腐。饭还没拾掇好,弟弟就早早地爬到炕上,看着刚刚端上的一小碗小豆腐,忍不住咽了几口口水,怯生生地望着父亲,虽然馋得够呛,想吃,却没敢动手。“吃吧,慢点吃,别烫着”。父亲话音刚落,弟弟就迫不及待地把小碗拖到面前,顾不得饭还烫嘴,狼吞虎咽地扒了起来。看见弟弟饥不择食的样子,父亲一句话也没说,母亲轻轻地连声叹着气,我强忍着眼泪,不敢流下来。我们都静静地注视着弟弟——父亲,母亲和我,个中滋味每人心里都知道。

在家住了两宿。我和弟弟一个被窝睡觉,搂着骨瘦如柴的弟弟,我偷偷地哭泣着,不愿叫弟弟发觉,更不敢叫父亲知道。那时我真不愿叫弟弟上托儿所了,可是又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哪有决策权?星期一中午,父亲叫我把弟弟送回托儿所。路上弟弟有说有笑,童心易逝也易回,才一天的光景,弟弟脸上又恢复了以往的笑容。一开始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到哪里去,当走到东关桥往北一拐的时候,弟弟“哇”地一声哭了,用力地拽着我的手,双脚用力地蹬着地,哭着,哀求着:“大哥哥,我不去。大哥哥,别送我上托儿所。”弟弟一哭,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哗地淌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发酸,胸口憋闷得直往上撞,无奈地拖着弟弟往前走,“去吧,不去还行?去吧,去吧,星期天大哥哥去接你。”
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无力地拉着弟弟的手,违心地劝着弟弟,真不知怎么哄他才好。弟兄俩边哭着边往前走,好不容易到了托儿所大门口。一进大门,弟弟哭声戛然而止,我抬头一看,原来托儿所的阿姨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弟弟胆怯地望着阿姨,阿姨板着脸,招呼着小朋友:“小民回来了,小朋友们欢迎。”(那天我才知道,托儿所里是称呼小名的)小朋友们面无表情齐声喊着:“欢迎小民。”弟弟仍然是怯生生地、无奈地望着我,眼泪再也不掉了,哭声更没了。望着弟弟可怜的样子,我的眼泪却止不住了。
送弟弟的时候正赶上吃中午饭。开饭时,做饭的师傅们先抬上一蒸笼萝卜丝,萝卜丝里边使上一点白面,因面太少,看着像净萝卜丝似的,每人分了半小碗,萝卜丝少得可怜,不够大人一口吃的。吃完萝卜丝以后又抬上一蒸笼小馒头,托儿所厨师的做功着实叫人佩服。馒头真叫小馒头,比酸楂稍大一点,虽小但是很秀气,约有一两重。当时我就想,难怪弟弟哭着不愿意来,吃这点饭好干什么?我们在家固然吃不到馒头,但是起码能吃饱了。过后我又想过,实在也不能怪托儿所的厨师,一月就12斤粮食,每天4小两,每顿一两粮,又不能上市场去买,不是难为炊事员吗?托儿所里虽然吃不饱,但在外人看来,人家托儿所里做馒头给孩子吃,实在叫人艳羡。那个年代想吃馒头,犹如异想天开。

1962年秋季,母亲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全家人仿佛见到了久违的阳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母亲病愈,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虽然清贫,但我们有了奔头。弟弟不上托儿所了,自己能在外边玩耍了。我在高密一中上初一,学校在火车站附近,离家3里多路,放学到家天就黑了。
弟弟天天傍晚时都在大门口转悠,看到我大老远就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仰起小脸看着我,“大哥哥”“大哥哥”的叫个不停。那个亲热劲让我永生不忘 。
可有一件小事却使我至今难以释怀,那是放学后的一个晚上,回家时,全家人都吃了饭了。我从锅里拿出饭来,一碗菜,一块地瓜面饼子,也不用放饭桌,放在锅台上就吃开了。弟弟围着我,不住地叫着大哥哥,时而从碗里抓点菜吃,我那天心情有点烦,放学又太晚,肚里没饭,更烦。看到弟弟又在伸手抓菜,我瞅了他一眼,冷冰冰地冒出了一句“你不是吃了吗?”。弟弟把已经抓起的菜一下子放下了,飞快地把小手缩回去,脸上的表情很尴尬。我仍然低头吃着饭,根本没考虑弟弟的感受,那时也不懂得什么叫考虑别人的感受,只是本能地想填饱肚子。弟弟不自在了一小阵,很快好像也没什么事了,仍然绕着我转来转去,和我说着他认为很有趣味的一些事,一口一个“大哥哥”亲切地叫着,弟弟曾经的窘态也没引起我丝毫愧疚。
事情过去多日了,每次见到弟弟迎我放学,心里就不是滋味,不自觉地想起父亲说的话。父亲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不只一次地说过,人哪有馋的?都是肚子里缺才馋,吃饱了喝足了谁还馋?
弟弟过世后,每当想起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就不自觉地联想起那晚上弟弟尴尬的表情和我冷酷的心肠,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碗里的一小口饭,小弟弟不自然的表情,围绕着我团团转的身影,我冷冰冰的语言……
忏悔的心情一直煎熬着我,我真想抱着小弟弟大哭一场。小弟弟短暂的一生,没吃过一顿可口的好饭!见到他最亲的大哥哥时,小弟弟只是想和我多待一会儿,陪伴着我一起说说话,看着我吃饭,他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依恋,没想到一个不自觉的小动作竟被我冷酷地吆喝了回去。
小弟弟去世后,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曾经不只一次地自责过,想着想着就流下了愧疚的眼泪。小弟弟,大哥哥为什么会对你那么冷酷?!

当我长大成人后,一看到五六岁的孩子,就想起我的小弟弟。自己的不管哪个孩子,只要是想吃的东西,只要眼前有的或者虽然没有但能办到的,我再也不会拒绝他们了,宁肯自己少吃点,或者不吃也要叫孩子们吃得舒舒服服,再也不会说“你不是吃过了吗”这样冰冷的语言了。曾经对弟弟的冷酷已使我悔之莫及。
最让我痛彻心扉的还是这一年的春天,一个黑色的难忘的春天。可恨天不假年,竟使弟弟和我阴阳两别!
平日,我和弟弟是一个被窝睡觉的。有一天晚上,弟弟突然说了一句:“大哥哥,你身上真凉。”我醒了,弟弟身上滚烫地热,那时太小不懂事,一会又睡了。弟弟难受上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我照常又上了学,也没跟父母说这事。回家吃饭的时候,不见了往常在大门口的弟弟。弟弟无精打釆地躺在炕上,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和笑容,饭一口也不吃,只 是一个劲地恶心。我竟然没问问弟弟感觉怎么样,也没试试他身上还热不热了。
我那时太小,脑子太简单,弟弟病得很重也不在意,吃了饭就上学。放学吃饭时看见弟弟痛苦的样子,也没往重处考虑。晚上搂着弟弟睡觉,只是觉得他身上滚烫,竟然一直没往心里去。就这样过了两三天的样子,有一天下午上自习课,教历史课的李河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说家里有事叫我回去。我的心咯噔一下子,但没想出是什么事。往家走的路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些凶多吉少的感觉,不然不可能不等到放学就叫我回家。心情复杂,脚步沉重,浑身像散了架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机械地挪动着脚步。快到家门口时,就见邻居有几个老太太在一起议论着什么。
看到我来了,北屋的张老太太说:“你弟弟……”到了这时我还没想到是怎么回事。赶紧到了家,眼前的一切让我一下子惊呆了,弟弟脸色煞白,嘴角上流着血水,紧闭着双眼,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母亲痴呆呆地坐在炕西头,父亲流着眼泪坐在弟弟身旁,他们谁也不说话,我痴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声也没哭出来,一滴眼泪也没滴下来,头轰轰地,木讷地站在床前,不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不相信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弟弟就这样没了。
当时我好像觉得还应该上医院抢救。正在我麻木地胡思乱想的时候,坐在炕沿上的西医刘生洁站起身背起药箱说:“就这么着吧,我走了。”我这才缓过神来,弟弟是真的没了!我可爱的小弟弟真的从此再也不能喊我大哥哥了,我再也不能和弟弟一个被窝睡觉了,放学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了……“哇”的一声,我嚎啕大哭起来,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了。母亲一句话也不说,父亲和母亲也不劝我,由着我大哭,他们知道,我最亲的人就是小弟弟,弟弟最亲的人就是我。一会儿父亲嘟囔了一句:“唉,这是来讨债的。”接着,耸动着肩膀不停地抽泣。看到两位老人悲伤的神情,看到小弟弟可怜的面容,真让我撕心裂肺的痛。

过了一会,二嫂的堂兄杜希月来了,他拿着一张铁锨,进门只是叹了一口气,把弟弟用小被卷了卷扛在肩上,顺手把铁锨递给了我,和父亲说了一句:“我们走了。”一路上我脑子里想着弟弟的一切,想起我扛着他走在黑暗的胡同里,想起他拾胡萝卜把儿吃时饥饿的双眼,想起他拽着我的手,双脚蹬着地不上托儿所的哀求,想起他一进托儿所看到阿姨后惊恐的目光,想起他一进托儿所嘠然停止了哭声的委屈相,想起他叫着大哥哥抓饭吃被我喝住了的尴尬表情,想起他从托儿所刚回家第一次吃饭前望着父母那既急切又胆怯的眼神……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不相信弟弟没了,觉得这好像在做梦。
我迷迷糊糊地跟着杜希月走到西门外韩信冢南面,选了一个地方,旁边还有许多小的坟头。杜希月挖了一个坑,把弟弟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然后填上土,堆起一个坟头。这一切都是杜希月干的,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是流泪。
埋完以后,我好像才回过神来,才知道从此再也看不到弟弟了。我望着坟头愣着:今后这就是弟弟永远的住处了?往回走的路上,我不住地回头望着坟头,拖着轻飘飘的脚步,昏昏沉沉回到家,父母亲也没问弟弟埋在哪里,我也没说话。人没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晚上做饭时,四弟放学一进门就呜呜地哭起来,看来他已经知道小弟弟没了,我又陪着四弟哭了一场。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摸被窝里空荡荡的,忍不住又哭起来,越哭越悲伤,哽咽着浑身发抖。父亲怕我的哭声会引起母亲的伤痛,蹬了我两脚,我不得不强忍悲痛,无声地流着泪,迷迷糊糊地一宿也没睡好。第二天饭也没吃就上学了。

弟弟走了以后,感觉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整天端详着弟弟的遗像,不住地流着眼泪。学习也静不下心来,上课时就照着弟弟的相片画像,满脑子都是弟弟的影子。很长时间没把情绪调整过来, 学习成绩一度下降很快。
弟弟去世后,我脸上几乎没了笑容,久而久之竟然成了习惯,整天板着脸,几乎没开心地笑过一次。有些和我交往不深的人,都以为我这个人难沟通,或是认为我这个人心肠冷酷。其实,他们怎知道,我的心是重的,脸怎能不是沉的呢!
弟弟岁数那么小,瞬间与我们阴阳两隔,真是连一丝一毫的心理准备都没有,谁能承受住这么沉重的打击?!
事情过去了很久,二嫂抽泣着向我讲述了弟弟临终前令人心碎的情景。她说,小弟弟临终之前,双手痛苦地抱着头,从炕东头爬到炕西头,又从炕西头爬到炕东头,口里拼命地喊着:“大哥哥,大哥哥,我要找大哥哥。”父亲上了班,大哥洗澡去了,二嫂那时已怀着孩子,行动不方便。母亲只是流泪,无奈地搓着双手,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在痛苦地挣扎。
弟弟一会儿用手死命地撕着头发,一会儿又用力地撕着喉咙,一会儿抱着头拼命地撞墙,一会儿又跪在炕上死命地用头拱着炕沿,最后,他绝望地瞪着双眼,十分痛苦地抽搐着,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哥哥,大哥哥——”在炕上窜了几窜,呲上了双眼,紧紧地咬着牙关,嘴角流着血水,瞪着眼睛直挺挺地倒下了……
弟弟临终时最想见的人就是大哥哥,他期待着大哥哥能帮他解除痛苦。或许他预感到自己不行了,渴望着见我最后一面。父亲懂中医,能救他,他不喊,生他养他的母亲就在眼前,他不喊。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想的竟然是我一他亲爱的大哥哥。可是我却在弟弟最需要我的时候,最想念我的时候不在他眼前,这种痛苦,这种悔恨让活着的人怎能承受得了啊!
弟弟长已矣,我却永悲伤!
每当想起这事,我就仿佛看到弟弟痛苦地撕着自己的头发,极端难受地、充满哀怨地、绝望地看着我……

弟弟去世35天的时候,我陪着体弱多病的母亲,去给弟弟上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坟。
沿着蜿蜒的小路,流着悲痛的泪水,滿脑子是弟弟的影子。母亲也和我一样,未到坟前就已泪流成行。
在我们这里,人去世后35天叫“五七”。据说“五七”之前,去世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五七”那天,去世的人非常盼望和自己的亲人见面。所以那天所有的亲人都要早早地去坟上,在坟前摆上祭品,烧纸,和逝者作最后的道别,用以寄托生者的哀思,安顿逝者的游魂。
来到弟弟的坟前,我指了指埋着弟弟的小土堆,话没说就抽泣起来。母亲颤抖着双手,把祭品一样一样摆好。祭品一共4样:一个带蓝花的碗里盛着两条很小的黄花鱼;一个纯白色的小碗里是炸的肉丸子,丸子下面都是白菜帮子,只是在白菜上面摆上几个调着白面活起来然后用油榨的丸子;一个带紫花的碟子里摆着几页桃酥点心;还有一个画着两条小红鲤鱼的白色的碟子里摆着几个橘子。那个年代,能准备这几样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从好几天前就偷偷地操办。因为父亲对喜事丧亡、请客送礼、烧香摆供等共产党不准的事从来不办,也不准家里的人办。母亲置办这些东西是背着父亲的,怕父亲知道了不高兴。
那些年,祭奠亲人是迷信。再加上生活困难,物资匮乏,有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活着的人都很艰难,哪还顾得上去世的人。所以尽管每年因病或饥饿死人不少但上坟的人不多,上坟又摆祭品的人家几乎没有。因为弟弟命苦夭折,死得可怜,因此再难母亲也要给儿子上坟并摆上供品。
烧纸前,母亲叫我围着小坟划了一个圈,祭品在圈里,纸也在圈里烧,据说这样做为的是不让别的幽灵抢了钱和供品。我很迷信这个说法,特意围着弟弟的小坟认真地用力划了两遍。我摸出火柴,接二连三地划了好几根,不是断了火柴杆就是被风吹灭了火,最后好不容易才划着,我用双手捂着差点又被风吹灭的火苗小心翼翼地刚把纸点上,母亲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念叨:小民,娘给你点钱,你不要乱花,给你点好东西吃,这些东西你以前没吃过,娘给你买的,馋了你就吃点,别一下子吃光了……娘好像在嘱咐还活着的弟弟,越说越难受,越哭越伤心。我在旁边陪着母亲,心酸,凄凉。

上坟之前,我还想过,母亲身体不好又有病,我要尽量克制点,别让母亲悲伤过度伤了身体。可母亲念叨的每一句话,让我听着绞心的难受,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到坟上,双手挖着坟土,止不住的嚎淘大哭。我仿佛觉着,弟弟就在我的身边,忧伤的目光正注视着我,凄怆的“大哥哥”声在耳边回荡。
我和母亲哭了很长时间,谁也没劝谁。最后还是母亲先止住了哭泣,默默地收拾着飘着纸灰洒满了泪水的祭品,我在坟前给弟弟磕了几个头,慢慢地站了起来,我和母亲谁也没说话,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家挪。我像下葬那天一样,不断地回头望着埋着弟弟的小土堆,总觉着弟弟还在。
到了家,母亲一头扎到炕上,又抽泣起来。我坐在炕沿上,陪着母亲悲伤,流泪。
弟弟去世很长时间了,我还经常幻想着弟弟会突然活过来。

50年了,每到清明节扫墓时,我就想起上坟时母亲嘱咐弟弟的话。那钱“你不要乱花”,东西“别一下子吃光了”,使我阵阵悲楚,思念弟弟的心情更加沉重。心里难受,就会流泪。白天经常想起他,梦中也常常见到他。每次梦中醒来,就觉着弟弟的孤魂在荒郊野外,孤苦伶丁地游荡着。
父母在世的时候,我家过春节不摆供品,不烧香,不烧纸。因母亲有病,连鞭炮也不放,只是贴上对联,穿上新衣服,吃几天饺子就算过年了。全家从来没在一起喝过年夜酒,没有别的人家那样的欢乐,心中怀着的全是悲哀和忧伤。每次煮出饺子以后,母亲都要在饭橱上摆一摆,然后再盛上一碗,拿上一双筷子,轻轻地和饺子一起摆到屋门口外。母亲每次放下饺子之后,都是含着眼泪念叨一句:“小民,这碗是你的,你在这里吃吧,吃上还有。”在寒冷的年夜里,我仿佛看到弟弟孤伶伶地站在院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吃完饺子,刚想往屋里走,被门神无情地挡在了门外。弟弟无奈而又渴望地望着屋里,在恍恍惚惚之中,在万家欢乐的年夜里,在别的人家辞旧迎新的炮竹声中,在天地圣众歆享人间牲礼和香火的时候,却躲在清冷的角落里,默默地任凭眼泪流个不停。
据说,每到过春节的时候,家里的人都要把自己先人的灵魂接回家过年。但是未成年人的灵魂是不能进供堂的。母亲可能想到自己的小儿子也会随着先人们回家过年,虽然进不了供堂,但总不能让儿子满怀希望回来,饿着肚子回去呀!母亲那么认真地摆上饺子,那么心酸地念叨着……我想,大年除夕那晚上,母亲最挂念的一定是我那凄苦的小弟弟。
弟弟去世后,父亲心里比我们更难过,也不只一次地自责过,这个教训对父亲来说太惨痛代价太大了。侄子和外甥患重病能转危为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用我弟弟的生命换来的。
父亲是开明人士,不准家里的人办那个时代不准办的事。他虽然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但由于爱子亲切,或许由于失子之痛,所以逢年过节,看到母亲把饺子摆到门口,等待自己可怜的儿子的灵魂回家过年的时候,也就默不作声了。
弟弟过世后,我也常常自责,弟弟和我那么亲宻,我的心为什么不细一点?为什么对自己的弟弟不多关心一点?那时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初中生了,竟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年幼的生命。弟弟的不幸夭折,是我前半生乃至终生最懊悔最痛心的事情!
5年前的清明节,我流着泪水给弟弟写了一个牌位,我不管什么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入祖茔的风俗,在上坟的时候把弟弟的牌位埋在父母的坟里,心里念叨了两句:“爹,娘,我把弟弟给你们找回来了。小民,你在爹娘面前要好好听话,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大哥哥每年会给你送钱花。”说来也怪,自从把弟弟的牌位埋到父母的坟墓里以后,心里好像轻松了许多,觉着弟弟离爹娘近了,有了归宿,我的心情不像过去那么悲伤了。梦中好几次梦见弟弟和爹娘在一起,弟弟仍然只有五六岁的样子,还是那么可爱,只是眼睛里多了几分忧伤,脸上一直没有笑容。
亲爱的小弟弟,大哥哥想你想得好苦啊!小弟弟,你知道吗?你走了半个世纪,大哥哥想了你整整的50年!大哥哥一直在想着你!明知道怎么想你也不可能回到我身边了,但仍然抑制不住要想!每当想到你时就止不住要流泪,也知道眼泪再多你也回不来了,但仍然要泪流满面!你的遗像我一直完好地保留着,等我百年之后我就带着你一起走,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好兄弟!
安息吧,亲爱的小弟弟。
安息吧,可怜的小弟弟。
安息吧,苦命的小弟弟, 大哥哥永远怀念你!
今年正好是弟弟去世50周年,满怀悲伤的心情,流着泪写了这篇悼念小弟弟的文章,寄托我的哀思。
一写于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