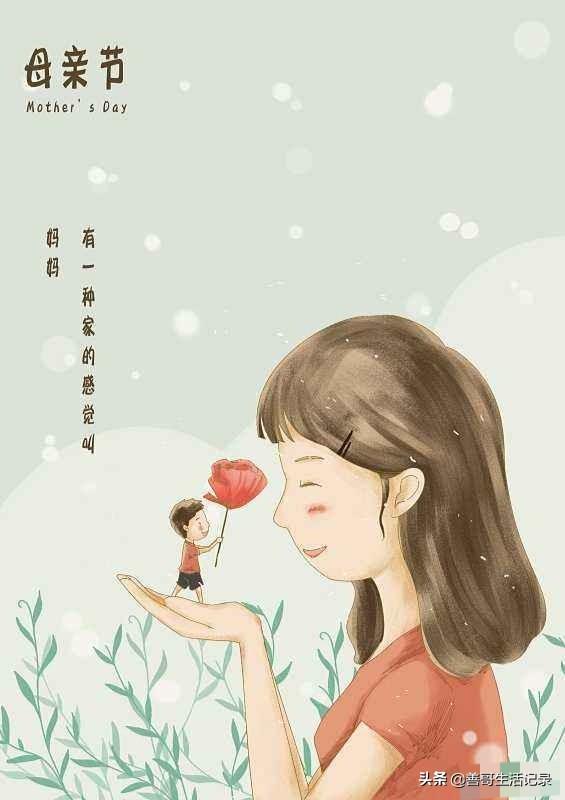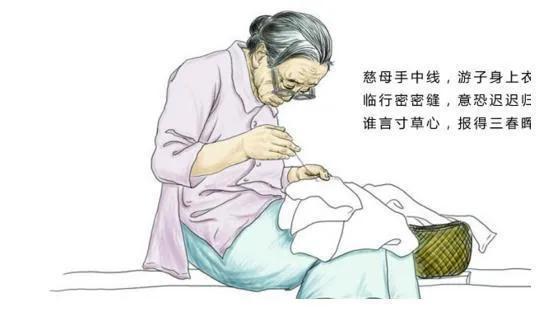清明|怀念母亲
周六中午,突然接到农村老家小妹妹的电话说,76岁的母亲因突发脑梗塞等疾病昏迷,已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了。我接到电话后,急忙从市里往老家赶。等我来到时,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
此时的母亲,已经是半昏迷状态,大脑不受控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我在母亲的病床前忙前忙后,母亲却问大妹妹说:“这个人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一会儿,母亲又对小妹妹说:“这个护士(把儿子当成了护士)杠好咧,对俺这么好,还叫娘。”到了晚上,母亲还不是很清醒,问我:“你是谁呀,对俺这么好,俺不认识你……”哎,母亲的话,让人听了心酸,生病生得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
母亲住院的第三天,稍微有些清醒时,就念叨孙女、儿媳,说男男(女儿小名)这么瘦,要让孩子多吃东西;小美(妻子)的腰(做过手术)怎么样了,当听说经常疼痛时,说小美可受罪了,要好好对待人家。母亲住院第四天,病情刚刚好转有点体力时,就非要让妹妹扶她下床,扶着床头练习走路,要早点自己照顾自己,生怕耽误我们过多的工作,好让我们各自早点回去上班。
母亲和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舍不得用。这次母亲住院自己所带来的被褥,还是30多年前,我当兵在家时盖过的红花洋布棉被子,其破旧程度让人难以置信,里里外外用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小碎布,缝补了近20个大大小小的补丁,就是这样,里面还露着棉絮。
现在,我们兄妹三个都早已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不在父母身边,都在外地有自己的工作,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条件远比父母强得多。但是,就是这样,母亲还是挂念着我们,我们每次回老家时,母亲都会把咸鸡蛋、鹅蛋、花生、大红枣等家乡的土特产准备好,让我们带回城里去。而我们带回老家的牛奶、糕点等东西,母亲却舍不得吃,经常是给这个留着给那个留着,时间久了,不是过期就是放坏、长毛变质……。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已经多年没有种植需要经常喷药、田间管理比较复杂的棉花了,但是,为了孙女冬天不受冻,做被子、衣服等要用棉絮,他们还是坚持种植了一小块地的棉花,收获后,到现在还一直放在家里,给孙女留着,随时备用。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这是第一次生病住院。自从我参加工作后,离开家乡30多年以来,由于工作繁忙离不开,这也是第一次6天6夜照顾陪伴在生病母亲身边这么长时间,真是亏欠父母太多太多了。
我已经50多岁了,最小的妹妹也40多岁,但是,母亲还是为子女着想,还是把子女当成孩子看待,从不考虑自己。这就是母亲,一生节俭,不言索取,只顾奉献,无论是健康,还是生病,总是时时刻刻挂念着自己的儿女,为儿女着想……
前年春天,母亲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我和两个妹妹就轮流回乡下农村老家照顾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让母亲吃好喝好减轻一点病痛。
母亲的牙齿不好,咀嚼能力差,硬东西咬不动,我就经常给母亲蒸鸡蛋羹,由于加水量掌握不准,蒸鸡蛋羹时,不是水加多了,鸡蛋羹太稀不成形,就是水加少了,鸡蛋羹太稠变硬口感差。为了给母亲做好鸡蛋羹,我特意从城内的超市里买了一个小白瓷碗带回家,专门给母亲蒸鸡蛋羹时用,一个鸡蛋一小碗水,蒸出来的鸡蛋羹不稀不稠正合适,鲜嫩好吃。
我们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几十米高的大枣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当兵离开家乡时,这棵枣树就有碗口粗细,枝叶茂盛,结的枣子又大又甜,小时候经常爬树上摘枣吃。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棵大枣树依然枝繁叶茂,夏天树荫能遮住半个院子,每年都会结不少的枣子。
每天清晨,这棵大枣树上就会落满麻雀、喜鹊、戴胜等各种鸟儿,密密麻麻,蹦蹦跳跳,飞来飞去,你叫一声,它叫一声,像是在议论,又像是在吵架,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一波刚飞走,一波又飞来,各种鸟儿叫声不断,这边鸟鸣还没有结束,那边鸟叫声又响起,此起披伏,美妙动听,心灵愉悦。每天清晨伴着鸟鸣起床,一天的新生活开始了!
虽然鸟鸣动听,但是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一天不如一天,刚开始还能自理,后来连大小便都得家人帮忙,还算壮实的母亲,让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尽管家人用了最大努力给母亲医治,但是母亲最终还是没能战胜无情的病魔,离我们而去……
现在,虽然母亲去世了,但是每当清晨听到窗外树上的鸟鸣声,就会想起在乡下农村老家照顾陪伴母亲时的情景,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仿佛没有走,没有离开我们,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壹点号 壹粉春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