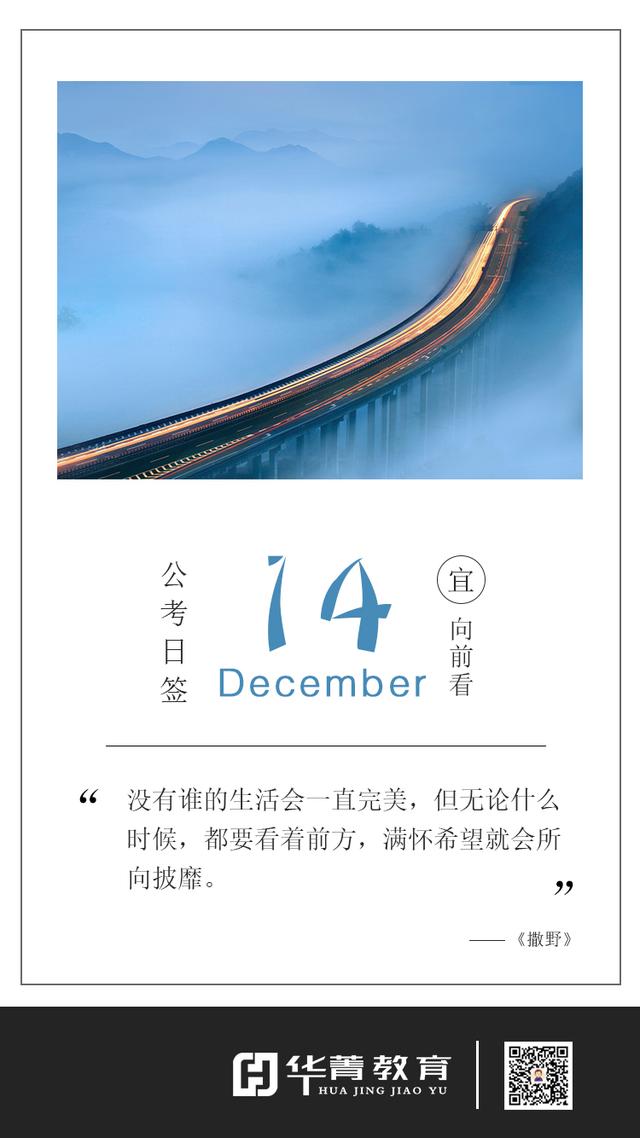战国秦汉之间,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担者和代表者;汉武帝以后,“经明行修”的儒生源源步入仕途,与文吏并立朝廷。汉朝上的政治势力,还有军功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等等。
然而在东汉一个新的官僚势力——士族门阀,在逐渐崛起,并在魏晋以下造成了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若干大士族在几个世纪中长盛不衰、垄断权势,成了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是如何在东汉发生的?很多人用庄园经济、依附关系和豪强地主来解释士族的起源;也有人认为,中古士族来自东汉清流、来自“地方名望家”,其崇高门第的根据,在于他们是“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并非全面。

古义的“世家”指“世世有禄秩家”,也就是世代占有禄位的家族。禄位是一种政治权势。若把社会权势也纳入观察,则社会权势既可以来自政治地位,也可以来自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世家”类型是多样化的。
官场有官僚世家,乡里有豪族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士族”的特征是“士”与“族”的结合。“士”即士人、文化人。古人又云“学以居位曰士”,“士族”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他们通过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了崇高门望。
从长时段观察,中古士族现象发生在一个“断裂”之后。周代世卿世禄传统,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众多古老的高贵世家衰败了,新世家的形成还有待时日。

在这个世家的“空档”中,社会一度呈现了鲜明的平民性,西汉尤为明显。皇帝刘邦来自底层,功臣们往往出身“亡命无赖”,权贵不乏起家卑微者,丞相公孙弘早年就是个放猪的。连母仪天下的皇后,也不避寒贱。汉武帝的卫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赵皇后赵飞燕,原先都是歌妓。
东汉就有所不同了,明帝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章帝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曾孙,和帝阴皇后是执金吾阴识曾孙,和帝邓皇后是太傅邓禹之孙。所谓“春秋之义,娶先大国”。皇后的出身也是个风向标,反映了“族姓”“门第”观念已浓厚起来。
可见,门阀观念从汉朝开始就已日渐形成。而门阀源于两汉地方大姓势力,他们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因而具有古老的农村结构的根源。

战国社会已存在一些非贵族的豪族右姓,他们役使子弟、宾客等等各种身份的人,与之形成了主奴和依属关系。汉初自耕农的数量大概是比较多的,但地方上也存在着各种豪族。有丧失了政治权势的六国旧贵族,也有利用权势巧取豪夺的官僚地主,以及由商贾兼并农民而形成的豪族。
东汉大土地所有制大大发展了。豪族占有大片膏腴之田,其中团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称宾客、部曲、徒附等,他们程度不等地在人身上依附于主人,务农之外还兼看家护院,战乱时随时能转化为私兵。
这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具有古老农村根源的家族势力,即乡里豪右。

豪族田庄比小农经济规模大,兼农、副、工、商为一体,也有适应生产发展的方面;豪右与依附农一定程度上也相互依存,不仅仅是剥削压迫关系。豪右兼并土地、武断乡曲、作奸犯科、隐匿人口等,破坏了地方行政秩序,导致小农的破产流亡。
汉代赋役以小农为单位,而且徭役重于田租,所以小农的数量和生计,事关帝国的财源和兵源。“皇帝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老说法当然也有道理,然而为维护行政秩序和编户体制,王朝也经常打击豪右以保护小农。
汉武帝任用酷吏的目的之一,就是打击豪右;王莽变法遭到抵制,很大原因是井田制侵害了豪右利益。光武帝大规模“度田”也以豪右为目标,可见帝国与豪右有矛盾的一面。

动乱中豪右经常起兵投机。秦汉之交的起事者还看不出太明显的宗族背景,但两汉之交就不同了,很多豪右、著姓投入天下逐鹿,出现了“部属宾客”“举族归命”“举宗为国”“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之类记载。光武帝刘秀与其兄起兵时所率领的,就是一个宗族集团。豪右若投机成功,就摇身一变为开国功臣了,进而成为东汉的显赫家族。
在汉魏之交,也能看到“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的情况。而若社会稳定,豪右参政就只能通过正常选官渠道了。“大姓子弟享有优先任用的权力”,成为郡县长官辟举的主要对象,因此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一些豪右并无朝廷名位。人们经常指责豪右“武断乡曲”,“武断乡曲”的意思就是“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一方水土”。另一类则是拥有朝廷官位的权贵,也就是河南、南阳附近的皇亲国戚。

前一种非权贵的豪右,纯粹是“古老农村结构”所滋生的,其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的数量作为任用资格。这类豪右不算“世家”,因为“世家”一词指的是“世世有禄秩家”,有官有爵有禄有秩才能算“世家”。
后一种官僚贵族豪右就不同了,他们的朝廷禄位像是一架扩音器,让他们在乡里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嗓音。这类豪右的权势,就不仅仅来自“古老的农村结构”了,也来自官僚政府。
因此在古老的农村结构形成的“乡里”场所之外,专制官僚政治提供另一个活动空间——“官场”。它构成了滋生“世家”的另一个场所。

外戚家族的煊赫在汉代特别突出。像西汉之吕氏、霍氏、王氏,东汉之窦氏、邓氏、阎氏、梁氏,都是一旦专权,则子弟亲党布列于朝廷。这是历史早期“家天下”传统的一种表现,并且西汉的军功阶层到汉武帝时就衰败凋零了。而东汉则不一样,从龙的元勋中有不少人权势蝉联,甚至与王朝共始终。
进而,新兴官吏中也逐渐积累着官族因素,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常常子孙相袭。
太史掌管着天文历算,需要高深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做太史,爷俩儿并称“太史公”。又如汉代法律浩繁,法学也是很专门的学问,所以法官往往出自“律家”,即法学家族。东汉颍川郭氏自郭弘以降,“数世皆传法律”,子孙中出了7位廷尉;还有不少担任刺史、侍御史、廷尉的,这些官都是司法监察之职。除了朝廷,州郡县也不乏这样的“世吏”。

然而时代居官,毕竟有可能形成门望。新式吏员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支配者,变成了一个官僚阶级,那么世代居官就意味着世代占有权势、利益、地位和声望。于是,先秦“世家”传统一度断裂之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世家”的缓慢积累,也就是官阀。
“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
东汉大士族,史家多以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为称。杨氏虽在汉初就有禄位,但西汉末就已衰落了。到了东汉,杨震年至五十才仕州郡,汉安帝时举茂才,由此百余年无禄位的杨氏,才发展起来。汝南袁氏家族的袁良,西汉末不过是二百石的太子舍人,其孙袁安以县功曹起家,后来官至三公,袁氏由此崛起。

无论杨氏还是袁氏,都不是先成为乡里豪右才变成当朝士族的。其家族后来在乡里的权势,倒是从朝廷权势派生出来的。
仅仅从“古老的农村结构”中寻找士族的起源,是一个方面,而 “官场”构成了另一个世家的摇篮。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官场”,它更为组织化、专门化,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
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