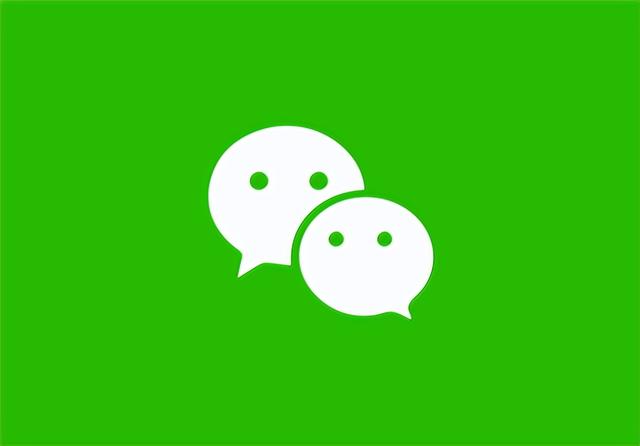↑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法官会遇到的问题?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法官会遇到的问题
↑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东营区法院 梁昊
言论自由:逻辑的力量与力量的逻辑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费加罗报》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以下简称《批评官员的尺度》)扉页上印着这样一行小字。初读此句,立有醍醐灌顶之感。试想,如果在一个无法自由批评的环境中,无论我们赞美的颂歌多么动听,也不能让公众信以为真,因为最真实的评价总是在可以自由批评的环境中产生。自由批评的环境是保障赞美言论公信力的制度土壤,失去了它,即使赞美确实出自人们的真情实感,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然而,批评不能没有边界,言论不能没有界限,言论自由的边界又在何方?
美国第一修正案的历史
1791年,美国通过了权利法案,其中第一修正案记载“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然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具体含义,却没有清晰地说明。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言论自由仅限于废止出版许可制,并不包含对于出版事后的免于追责。为便于事后追责,便创制了一个罪名——煽动诽谤政府罪:只要认定被告存在主观恶意或有不良企图,便可裁定“煽动诽谤政府罪”成立。事实越是有力,诽谤罪行越是严重,因为“一个言之有据的批评,比不实之词更能损害官员威信”。 1798年美国国会通过《防治煽动法》,宣布批评联邦政府的行为构成犯罪。在《防治煽动法》生效期间,某种言论只要被认定有“不良倾向”,就可以为维护社会利益追究言者责任。言者因言获罪。所幸,该法只有三年的有效期。
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治间谍法》。该法出台一个月后,便引发了“《群众》杂志案”。勒尼德•汉德法官判《群众》杂志胜诉,他在该案中认定:言论只有在直接引发违法行为时,才应予以制裁。本案最大的创举是将有敌意的批评也列入了自由言论的范畴,认为言论自由当作最大的社会利益,是赋予政府合法性的权力之源。之后,在“艾布拉姆斯案”、“申克诉美国案”等案件中,霍姆斯发布了异议意见,提出了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并对此进行了解释。之后,霍姆斯大法官连同布兰代斯大法官不断就《防治间谍法》案件发出异议,并使美国人民与最高法院承认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的基础价值。在“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首次确认权利法案适用于各州,改变了183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定“权利法案”各项条款仅适用于联邦政府,而不约束各州的情形。
在这之后,“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布里奇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更是进一步拓展了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沙利文案”中,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其实质意义便在于将错误言论也包含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自“沙利文案”之后,与第一修正案有关的法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高法院也通过判决不断丰富修正案中的言语。
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一代又一代的大法官通过缜密的思考和精确地判断,不断拓展着言论自由的含义,说服并教育着美国民众接受对于言论自由的定义。其实,该书对于美国第一修正案历史的梳理以及对于沙利文案的探讨,都是力图回答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自由的边界
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何处呢?更具体一点,言论自由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界限何在?有人赞美美式的自由,有人欣赏这种自由,有人批判这种自由。但就《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中透露的信息,这种自由,是美国200多年历史的积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我们,虽可以借鉴其对自由的定义,却更需要找到我们自己对自由的定位。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言论自由创建了新的平台,与此同时,司法与这些“自由言论”的碰撞层出不穷。2006年彭宇案、2008年杨佳案,2009年邓玉娇案、李昌奎案,2010年药家鑫案、李启铭案,还有最近的李天一案。汹汹言论不断影响、左右甚至决定着这些个案的司法,将一个个由法院裁决的案件变成让公众评判的“事件”。
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虽然其所遵循的逻辑原则和推理进程有所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案件审理及判决的逻辑自洽性。在审理过程及判决书中,法官应当严格遵循三段论的推导规则: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得出结论,这应当让审理过程及判决得到当事人及公众的普遍认可。换句话说,法官应当用逻辑的力量“征服”所有受众,让公众在理性的指引下,通过缜密的推理,得出与法官判决相同或近似的结论。然而,囿于各种情势,或许法院审理过程不够公开,公众认知的事实与法官通过推理得出的法律事实有出入;或许法官与公众、专家对于法条理解的偏差;或许没有经过严格法律逻辑训练的普通人推理走上歧路。这些都让网络、社会得出的信息、结论与法院的判决差异较大。从而不断将司法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逻辑的力量似乎在我们的社会中失去了支点。
逻辑的力量退缩了,使得法院的公信力降低,更致命的是,在此衍生出力量的逻辑。
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其实自一出生便是与“权力”连接在一起的连体婴儿。纵贯近几年来影响较大的几个案件,考察其运作模式,不外乎一种:利用自由的言论空间,在媒体、网络上或发表没有根据、或以偏概全的言论,或以不符合逻辑的推理误导民众,或迎合民众对于“特权群体”的情绪,使某个案件成为社会热点,获得“点击量”之后,便盗用民意的名义,向法院施加压力,迫使其迎合这一小部分人的价值;或向有关部门施压,使其对法院的裁判做出干扰。在这里,没有逻辑的存在,谁占有疯狂的“点击量”,谁就是赢家。这,就是力量的逻辑——谁占有力量,谁就代表着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权力被“言论自由”所绑架,情绪化的宣泄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被异化的权力又滋生出各种“自由的言论”,司法的独立有时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权力”。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辨明,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逻辑。能经得起缜密逻辑的严格推敲的言论,即使是逆耳的批评,也应为他们提供完整的表达空间;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推理出的言论,即使是甜美的赞歌,也应限制或拒绝他们出自人口。
我们,生逢其时
吉洛特案是美国“恐共风潮“的产物。霍姆斯大法官面对他人质疑他“袒护共产主义言论”时,他在异议书中写道“从长远看来,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终究会被社会主流接受,言论自由的唯一含义,就是给予这一理念被传播的机会,使他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美国的法官在异议中流露出的自信与坚决,对今日的我们仍有启示意义。当我们明确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之后,能否树立霍姆斯大法官这样的自信?当我们面对异议时,能否用逻辑的力量阐述其不合理之处?
然而,自信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自信来源于实力,在面对批评、异议之时,这份实力取决于我们会不会、能不能用理性的思考来接受批评或反驳其不实之处。在面对部分媒体、舆论的“口诛笔伐”之时,这份实力在于我们的法官能否用充满逻辑的推理说服公众接受我们的结论。在面对情绪化的指责、哭诉、威胁之时,这份实力在于我们的法官能否用谆谆教诲,说服他们认可我们的推论。能否让力量的逻辑向逻辑的力量低头,能否让不当的权力为正当的权利让位,能否让自由、理性的言论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生逢其时!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微信ID:dongyingzhongyuan长按二维码关注微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