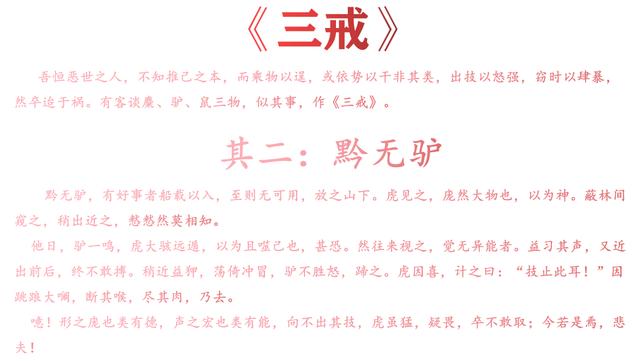2016-03-27 01:06 北京晨报 我要评论0

《文章皆岁月》
作者:萧乾
出版:重庆出版社
1939年,我从香港《大公报》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现代汉语。
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工资一律都是每小时两毛五分。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教汉语认识了美国的威廉·安澜,合编了八期《中国简报》,这些都已写进我的《文学回忆录》中了。这里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为了谈谈我通过教西方人汉语——特别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不少人主张教外语要用直接教学法,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我也同意。我从9岁跟我的洋嫂子学英语,就是这么用直接交谈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三我才读了一本语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个旅人看地图,地方去过了,就一目了然。还记得我那本语法是带图解的。至今,我仍认为用图解是学语法的一条捷径。
但是,教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华语,我认为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语法是由活的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语言结构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词类。
我在东方学院教的课本似乎是上世纪30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编的,他还曾把会话部分录了音。当时,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直到1941年才教了一批(40名)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仰上(如桂格会)的反战主义者。上次欧战,英政府曾把当时的反战主义者全都囚在海峡的曼岛上,他们受罪,对国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费。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办法改了,准许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职务。这40名青年就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训练班,由桂格会提供场所——伯明翰郊外一所农场,由我和西门教授给他们开个速成班。我除了语言,还得做一些有关中国各方面常识的介绍。
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这40名英国青年应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还有行动:拒服兵役。第一次欧战,英国处理得十分简单化,也十分浪费。国家同敌国开战,全国同仇敌忾,可却有一小撮人出于信仰,同抗敌大唱反调,拒不服兵役,关进牢房当然罪有应得!然而25年后,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中学乖了,懂得矛盾应缓解而不应激化,也承认既然宪法上给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为执行宪法的政府,就应认真实现,方能取信于民。
在我同这批反战青年接触的40天中,我深深感觉他们都是诚恳的、优秀的英国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编一份艺术刊物,还有搞医的。近年来他们时常把看过的英国报刊寄给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在滇缅路上英勇献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贝利,在云南内地染上恶性疟疾,一条腿致残,一直架着拐。多年来他疾病缠身,却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1995年11月26日去世。(二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