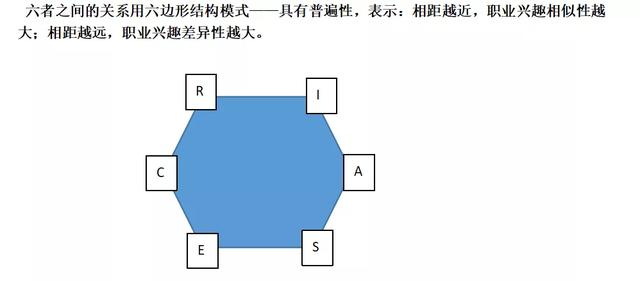今天上午几个人一起去看望了癌症晚期的那位同事,病情发展得很快, 十一之前还能坚持上班的,虽然摇摇晃晃的。
那天,他扫码进厂区,门卫见了,还打电话到相关部门,说,“他这种情况,你们还让他上班啊?倒在院子里怎么办?”
负责考勤的主管,那天就直接跟他说了,别来上班了,他当时头脑已经不清楚了,答非所问,思维都有些混乱了。
我开车把他送回了家,也安慰他,还是在家静养吧,十一假期加上休假,再请个病假,坚持到年底52周岁办理病退也是可以的。
也许人到了这个地步,心境是很复杂的,他特别渴望上班,虽然身体上已经绝对不适合,你善意地劝他,他反而会误解。
在工作场所,包括我在内,已经看到他跌倒三次了,而且跌倒后自己爬不起来,浑身瘫软的像个面团,抱起来都费劲。
可当他老婆劝他在家休息时,他又很生气,坚持说自己能上班。
他身患肺癌晚期3年多了,一直靶向药 中药调理。2个月前,几个阶段的靶向药都失效了,开始介入化学治疗,但效果很差 ,人也很痛苦,一周就要去化疗一次,精神状态迅速萎靡、凋谢。
他十一前,上衣穿着棉衣,下身穿个短裤和凉鞋,就来了,这个状态来单位,谁又能再给他布置工作呢?
他摁一下电脑开机键,都费劲了。
昨天他老婆打电话给我们,求我们能否组织出面,帮他找一家好一点的安宁医院,送他最后一程?
说实话,这方面,我们也没啥资源,尤其进入临终关怀阶段了,三甲医院、区、街道医院都不收治了,因为高强度的对因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养老院能不收,因为算她们的死亡指标。
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然而,在医学和人力不可为的时候,走向死亡总是令人感到无奈的。
各方打听了一下, 我们国家的临终关怀,或者说叫安宁疗护,专业人员奇缺,相关的服务机构供不应求。
当寿命只有两周,更多的是以护士为主导,按小时到天进行善终服务,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
这方面,我们距离发达国家还相差较远。如何实施临终关怀,维持人生最后的尊严,在生命的尽头与死亡“和解”,实在是一个沉重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农村,这样的情况,都是拉到家里,放在堂屋,叫来所有的子女和至亲,头对着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在城里,临终关怀反而没有农村更有亲情的味道,稍显冷漠,因为人少、都是钢筋丛林的森林。
今天我们去的时候,同事正好又昏迷了,醒来后双目无神,已经认不清我们了,看到年底才52周岁的他,短短半个月,瘦了十几斤 ,脱相了,真的很难受。
他老婆说,除了剧烈的癌痛外,他的皮肤已溃烂、散发恶臭、大量的腹水、大面积的浮肿、严重的黄疸、大小便失禁......
我们学了30年的唯物主义,有时想想,有个信仰、寄托的话,走的时候,是否会安宁一些?
100天前,我母亲去世前,她晚年笃信的JD教的三个教/友来看她,在床前握着她的手,给她唱赞/美诗、圣/歌,十分同情,我觉得对她的疼痛和恐惧,是极大的安慰。
我老婆在一家公办养老院工作已经十来年,那个400 床位的养老院分为养护区和护理区,养护区都是65-80岁左右,自己能动的,生活质量还行,护理区是70岁以上生活无法自理的,大多数陷入失能状态,生活质量很差,一个护工要照顾3-6个老人,顾不过来。
这些老人的临终关怀,主要靠护工、护士,专业的服务很少,家属也都倾向于老人在养老院待到最后一刻,想一想老人临终前的景象,真是很难过的,亲属也是一样煎熬。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多少人可以从容面对生死?
当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走到生命末期,伴随着癌症晚期遭受种种折磨,治与不治之间,我们对自己、对亲属如何做出生死决策,我们还能为生命做些什么?
如何做到逝如秋叶之静美?如何消除患者和亲属对死亡的恐惧,抚慰他们的心灵,让病情无法逆转的患者坦然而有尊严地离去?
“临终关怀”、安宁疗护,体现了人性的温暖、社会文明的程度,又透着多少祈求和无奈!
真的需要向从事临终关怀的医务工作者深表敬意,并希望这样的生命尽头的“摆渡人”越来越多。